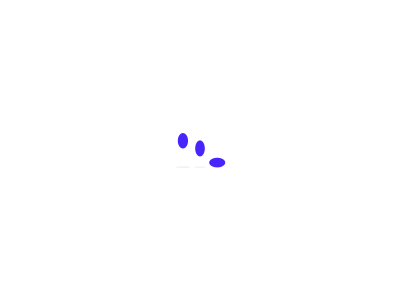“重构”建筑物
蔑视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物家包括机器派也大致遵守的原则——提出了挑战 1,一批建筑物史上不同凡响的、以“杂乱”“残缺不全”“突变”“取法于”和“气势雄伟”为特色的新形式登上建筑物大舞台。由于后现代主义讲究长幼有序、和谐统一的建筑物价值观念早已经被特别强调机能第一、呆板的后现代主义所摧毁,而到了后现代主义也快要被黄金时代抛弃时,已经没有甚么东西能用来约束建筑物师的“想像力”了。当代的建筑物师们每一人都渴望要成为勒·索绪尔耶、伊萨和赖特那般的建筑物蜘蛛人,每一人都希望自己的建筑物能像Sivaganga那般世界闻名,至于Sivaganga并不是一座机能合格的音乐厅那又如何呢?他们发现自己如果有足够的耐性,如果能够用各种常人难以认知因此感觉深不可测的营销说辞去打动商人和当权者,抓住此时此刻的眼球效应,甚么样的“思潮”“流派”和“主义”都能被发明出来,“后后现代主义”是其中之一。自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开始启动的建筑物师帕尼诺区的地位现在达到了辉煌的三角形。在许多地方许多人看来,建筑物表演艺术是一门奇观的表演艺术,建筑物结构设计的唯一目的是引发别人的惊叹。用埃文斯·芒沃特(Lewis Mumford,1895—1990)的话说:“图章”取代了“画像”。
大卫·杜伊斯堡曼

美国建筑物家和理论家大卫· 埃 森 曼(PeterEisenman,1932—)是最早“鼓吹”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建筑物家。他的结构设计理论比较复杂,就连莫里斯·沃克这位建筑物领域的沙场老将都承认自己“无法追踪其哲学思维结构设计的范围”。[60]150 要想确实搞清楚杜伊斯堡曼所主张的后后现代主义究竟要做甚么或者说要“肯定”甚么,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建筑物评论者詹姆斯·詹斯特(Charles Jencks,1939—2019)曾为其归纳了四个要点:Arnoldi(Not-classical),否构图(De-composition),无中心(De-centring)和“反连续性”(Dis-continuity),或许从这样一种“否定”的角度才能比较好地认知杜伊斯堡曼和他的后后现代主义。
1967 年,杜伊斯堡曼成为位于纽约的建筑物与卫星城研究所(IAUS)第二任主持人。这是一家非营利和没有学位专业学位的建筑物基础教育研究机构,旨在为那些有意寻求现代基础教育之外替代方法的学生提供建筑物、景观和卫星城结构设计的交叉学科。在杜伊斯堡曼任职的15年间,IAUS 首创了一种高度特别强调创造特质的建筑物教学方法,把自由创意、夸张造型和愤世嫉俗当作是建筑物意念的源泉,包括屈米、托德、马利克德、库伊萨和里布里斯班金在内的许多日后大名鼎鼎的建筑物家都曾在这里参与深入探讨或者深造学习过。
1989 年建成的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大学韦斯特纳表演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for Arts)是杜伊斯堡曼的代表作。三套偏差12.25°分别对CQ45与校园的分层两方地穿插建筑物之中,将建筑物垂死,搅得千疮百孔。建筑物内部不同内部空间都拥有各自的梁、柱体系,在内部空间黏合之处毫不留情地交错在一起,公然蔑视一切现代的建筑表演艺术构成和使用法则。建筑物评论者安德鲁·巴兰坦(Andrew Ballantyne,1956—)形容它“用对人类的敌意”来形成建筑物师个人的风格。

1999 年开工建设的西班牙圣地亚哥·德·贡波斯代拉郊区的加利西亚文化之城(City of Culture of Galicia)将圣地亚哥老城肌理与基地的山形进行叠加处理以形成丘陵似的建筑物群。杜伊斯堡曼说:“通过这种制图式的操作,这一项目显现出来的是一个弧形的地表。它既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地面;既是成形的地面,又是成形的建筑物。圣地亚哥的中世纪历史出现在这里,但并不是代表怀旧,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出现。它是崭新的,却并不陌生。”“既不是”“也是”,“既是”“也不是”,是与不是全在建筑物师口舌之间,这是杜伊斯堡曼和后后现代主义结构设计理念的生动写照。

这座文化之城有着宏大的构想,但经过10多年漫长建设,在建设费用超出预算一倍以上而所吸引的游客却寥寥无几的情况下,2013 年,这个当代典型的、试图靠奇观形象工程来发展旅游的项目,在一片批评声浪中被迫宣布半途完工,原定的国际表演艺术中心等项目不再建设。
伯纳德·屈米

瑞士建筑物家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1944—)也是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拥护者之一。他于 1982 年结构设计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Parcde la Villette)是后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早期代表作。点、线、面三套各自独立的体系并列、交叉、重叠,成为结构设计的主要构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点”,屈米将之处理为一系列名为“疯狂”(Folie)的红色构筑物,它们以间距120米的矩形阵列空降在公园中,造型不考虑特定的机能,你能将之用作餐厅、展厅、售票亭或游乐场,也能完全将它看作是抽象的雕塑。

英国建筑物评论者希拉里·弗伦奇(Hilary French)评价屈米和杜伊斯堡曼的这些建筑物是“精神错乱”,是“只有‘思想’,没有‘机能’”的东西。应该说,一座卫星城中偶尔有几座这样的“反建筑物”存在,也许能把它们当作卫星城雕塑,或者用屈米自己的形容叫作“卫星城发生器”(Urban Generator),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刺激卫星城的活力,但如果满目皆是就一定会让人发疯了。

弗兰克·托德

加拿大出生的美国建筑物家弗兰克· 托德(Frank Gehry,1929—)是后后现代主义建筑物家中最突出的一位。在默默无闻了半辈子后,1978 年,年近半百的托德在洛杉矶附近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建造了一座造型奇特的自用住宅(Gehry右侧为厨房采光窗托德住宅朝向主要街道的入口外观,托德住宅厨房内景Residence)。它原本是20世纪20年代建设的带门廊的普通木造房屋,托德在改造时有意将构成建筑物的一些元素进行分解,而后再以看似杂乱随意的方式进行重新组合。比如厨房和餐厅的“采光部分”就被从墙体上分离出来,然后仿佛从天上跌落下来,刚好把厨房屋顶砸开以行使它应有的机能。又比如门口的台阶,好像刚从自卸卡车上倒下来的一样“胡乱地”堆叠在门口。这座将70% 的邻居吓到搬家的标新立异的建筑物令托德一举成名,确立了他后半生的结构设计风格。对比一下米尔斯对待自己第一座建筑物引起争议时的态度,只能说黄金时代不同了。


1987年建设的位于德、法、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畔威尔(Weil am Rhein)的维特拉结构设计博物馆(VitraDesign Museum)是托德后后现代主义的成熟之作。维特拉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家具制造商。这座建筑物的一大半被肢解成各种部件:雨篷、楼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外观、天窗等,在被赋予迥异的造型后再重新组合,仿佛是一个具有特殊体量和能量的、“蠕动中”的生命体。

从后后现代主义到奇观建筑物只有一步之遥。1997 年落成的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是托德建筑物生涯中最受世人推崇的杰作之一。这是一座非借助计算机而无法完成的“黄金时代造化”,由于造型是如此不规则,以至于工程技术人员抱怨说内部没有两个钢构件的长度是完全相同的。《纽约时报》当年发表建筑物评论者赫伯特·穆尚(Herbert Muschamp)的文章,毫不掩饰对这座建筑物的顶礼膜拜:“传言说奇迹仍会发生,而且有一个奇迹就发生在这儿——这是我们尖叫欢呼的理由,让我们失去克制,把帽子抛向天空……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一座自由联想的圣所。它是一只鸟儿,它是一架飞机,它是蜘蛛人,它是一艘船,一朵菊花,奇迹的玫瑰,玛丽莲·梦露的再生……掐一下你自己吧,但不要醒来,好让你继续这一梦想。”这座建筑物开创了奇观建筑物新黄金时代。它为毕尔巴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建成后的头三年,前来参观的游客就接近400万人,让这座此前默默无闻的小城一跃成为西班牙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形成了所谓“毕尔巴鄂效应”,也成为全球众多卫星城争相效仿的榜样。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建造在卫星城沿河的旧货运火车站搬迁后的空地上。一般来说,欧洲卫星城居民对他们所在卫星城的历史氛围是非常珍惜的,即使在旧城生活需要忍受某些生活上的不便,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感情。在这种地区,即使是要建造一座怪异的建筑物,也必须要顾及周围的环境脉络。比如1996 年建成的捷克布拉格的“舞蹈之家”(Dancing House)是这样的例子,尽管形状怪异,但能够有所克制,基本上能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共同维护街道和卫星城生活的正常秩序。

但是在美国的某些卫星城氛围已经大大削弱的地方, 因为没有了约束,托德就能尽情地施展手脚,丝毫不用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2000 年建造的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Museumof Pop Culture)以及 2003年建成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Concert Hall)都是这样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些卫星城的郊区化进程。托德在同矶崎新的一次对话中坦承,在他心目中建筑物与雕塑的区别仅仅在于“能开窗采光的是建筑,而雕塑不能。”对于许多崇拜者来说,托德结构设计的建筑物个性非常鲜明。不过也有人认为,托德不过是在个性化的名义下,在世界各地“栽下”一堆又一堆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招鲜中的一招鲜,自我抄袭、手忙脚乱的姿态设计,在毕尔巴鄂、洛杉矶和西雅图这些地方一堆堆地栽着,不管在哪儿看上去都一样,在哪儿都显得格格不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如果说,国际风格黄金时代满世界都是火柴盒的话,今天不过是换了一种样子在全世界流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当年,国际风格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派敬仰之情,如今这种崇拜又会持续多久呢?时间将会是检验建筑物最公正的裁判。“谁又能保证今天被捧为诗意个性化的珍宝,以后不会被批评为四处泛滥的恶劣而媚俗的作品呢?”

扎哈·马利克德

出生于伊拉克的英国建筑物家扎哈· 马利克德(Zaha Hadid,1950—2016)是当今世界女性建筑物家中的佼佼者,是堪与高迪相比的历史上个性最为鲜明的建筑物家,也是当代最受年轻一代推崇的建筑物巨星,却在刚刚步入创作生涯高峰时不幸英年早逝,殊为可惜。
马利克德的成名作是1982 年创作的香港山顶俱乐部(Peak Club)结构设计方案,被评价为“有如爆炸中的建筑物碎片,以锐利的弧线、强烈的动感、震撼的力度,在宇宙内部空间中飞舞”。这个后后现代主义特征明显的结构设计方案由于得到矶崎新的大力推荐而获得评审第一名,虽一直未能建成,但却使马利克德一举跻身世界建筑物明星行列。

1993年建成的莱茵河畔魏尔的维特拉消防站(Vitra Fire Station)是马利克德第一项建成的作品。维特拉公司曾受火灾重创,因而萌生修建专用消防站之念。这座消防站由几个极具动态的体块穿插而成,分别用作车库、训练室、更衣室和办公室等不同用途。入口处一片锐利如刀刃的房檐向外剌挑而出,特别引人注目,仿佛爆炸中的建筑物碎片,实现了香港山顶俱乐部结构设计方案的基本构思。


马利克德常说:“我自己也不晓得下一个建筑物物将会是甚么样子。”她的结构设计总是给人异想天开的感觉,所以许多方案在获得建筑物专业人员好评之后却不得不停留在图纸上。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得到改变。2004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物奖的女性,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建筑物项目。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她的建筑物风格发生转变,借助计算机软件参数化结构设计,从略显杂乱的后后现代主义风格转向大体量流线造型,并由此获得“曲线女王”的美誉。

马利克德的建筑物极具雕塑感,曲线处理生动细腻,无人可比。这种造型如果用在空旷的城郊,或者是小型展馆、车站之类的小体量建筑物上,比如2011年建成的格拉斯哥河滨博物馆 (Riverside Museum),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效果都是很好的。或者如果能够对周围的建筑物环境有更多的照顾,就像她在罗马所做的国立21世纪表演艺术博物馆 (MAXXI)那般,对卫星城景观和卫星城生活都会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但是在那些缺乏约束的地方,比如2014年建成的首尔东大门结构设计广场,展现出来的却是奇观建筑物黄金时代的张扬、挥霍以及对卫星城现代肌理的蔑视,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雷姆·库伊萨

荷兰建筑物家雷姆·库伊萨(RemKoolhaas,1944—) 是奇观建筑物黄金时代最有名气的明星建筑物家之一,是马利克德在伦敦建筑物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Architecture)求学时的老师。西雅图中央图书馆(Seattle Central Library)和北京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是他的代表作。

库伊萨还积极投身于理论著作。1995年出版的(S,M,L,XL) 是他对于奇观黄金时代建筑物环境的概述。他将所有企图确立都市秩序的思想都看成是一场演给人看的假戏,他说,“进步、身份、卫星城以及街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也许会让人释怀得到解脱,因为“一切都结束了,卫星城的故事演完了,卫星城已经不再存在了,剩下的不过是串在一起的破烂”。这样一种对待卫星城和街道极为“消极”的观点很能解释他以及当代众多明星建筑物家在许多卫星城中的所作所为。
丹尼尔·里布里斯班金

出生于波兰犹太家庭的美国建筑物家丹尼尔·里布里斯班金(DanielLibeskind,1946—)也是奇观黄金时代的明星建筑物家。由他于1989 年结构设计中标的柏林犹太博物馆(JewishMuseum Berlin)是德国政府为深刻反思20世纪上半叶那段可耻的历史而兴建的。曲折不定、动荡不安的建筑物形态仿佛一曲凄凉的乐曲——里布里斯班金少年黄金时代曾受过音乐方面的专业训练——讲述着犹太人被驱逐被屠杀的那段令人潸然泪下的惨痛经历,建筑物表面鞭笞般的深深裂痕在银光闪闪的镀锌幕墙上显得尤为刺目,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将之抚平。

这座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建造开创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的创伤纪念主题博物馆建设风潮。里布里斯班金本人也在此后承担了多座博物馆的结构设计工作,其中包括2006年建成的丹佛表演艺术博物馆新翼汉密尔顿馆(Hamilton Building at DAM)。里布里斯班金在描绘他的创作理念时说,当这一结构设计概念“降临到我的头上时,我正在飞越落基山脉上空,于是我就把舷窗外的山体形状拷贝到我的结构设计中去。我受到了落基山脉光线和地理形态的启发,但给予我意念更多的是丹佛人民那宽广开放的脸庞”。听上去十分感人。里布里斯班金在评论自己的结构设计思想时说:“我为谁而建?我认为每一座建筑物都是在和那个不在那儿的人对话。每座优秀建筑物的对话对象,不是公众,不是那些在建筑物边走过或是使用这座建筑物的人。它的对话对象是在两种意义上未出现的人——那些生活在过去的和那些生活在未来的人。我认为那些才是建筑物的对话对象,那才是让这座建筑物变得重要的人。”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哲理,可是仔细想想,又有些不知所云。这或许是当代明星建筑物家的惯用逻辑吧。英国建筑物评论者汤姆·迪克霍夫(Tom Dyckhoff)不客气地指出:“他的结构设计,好像是在兜售一批可供出租的公寓。同样的建筑物形态,既能用来象征犹太人的流离失所,也能用来形容荒野开拓精神,这就让这些象征作用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指责确实有些令人难堪。如果仅仅是凭借说辞来赋予建筑物内涵的话,那么许多时候真是不堪一击的。

注:
本文来自陈文捷先生的著述、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新书《多元的黄金时代:从启蒙运动到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