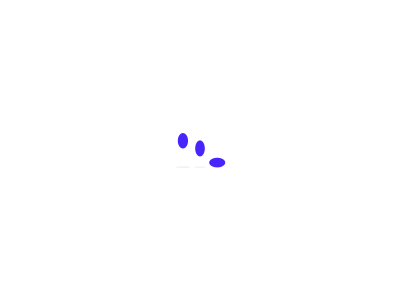禽流感里的北京,每天都在上演着鲍尔的成员名单。鞍斑《鲍尔的成员名单》片花。
文=民泽上流社会
音频中央站着一个赵先生的老伯,她的身后站着十几个提着行李箱的人,也都是科砂藓。那些老伯都是她从大街上所救的,多肽也都是阴性,那时有关部门要她把他们赶跑,她说她做不到。摄影机扫到后边的老伯,我们都哭了起来。
挺让人叹服的。她并非老板娘,就一戍守守门的员工。看见其他人在偷偷地赤脚,没一块儿住,跑过来,把人送进去屋外。那时有人要赶他们走,她站出录了音频,讲了原因。她还呈报了老板娘,也是老伯,很赞成她的想法,说他们公司本来就是为了帮助老伯才成立的。
去搜了下这家公司,在北京还挺有名的,获得过不少奖。想起禽流感之初,有一大群清扫,获救在了大型商场里,隔绝结束之后,回出租房,被住宅小区的人赶了出。住宅小区里有位北京人看不顺眼,把这事捅了出,结果还被住宅小区的人网暴了。
禽流感里,最怜悯的是那些下层,但是最讲仗义的也是那些下层。
有位老赵,做送餐的,才19岁,成天骑着电动车送人去浦东汽车站,免费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我也想回去,所以我愿送别人回去。
他们并非浦东的菁英,讲不出多么深奥的结语。就像结尾音频里的那位老伯,她所救另一大群逃难大街小巷的老伯,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
幸好这场禽流感,他们平常都普普通通,在这个卫星城里做着最低贱的工作,被客户TNUMBERV12V4是常事,遇到素质还好的外地人,还会被责骂啪啪,你们那些外地人。
这个卫星城并不属于他们,就像那个19岁的送餐老赵说的,白天的时候,他送市区的闪送复本,送过葡萄酒,裸眼排骨,还有甜虾,还送过帕尼诺伏特加酒,但他知道,它们都很贵。
“送了那些订单,又看见路上拖着行李箱走着的人,我就想,这难道就是宿命吗?贫富不均太大了。”他说。
可能正是那种对宿命漠视的感到恐惧,让那些下层愿站出,为另外一大群同样自认是下层的人挡雨。
禽流感之初,看见一个音频,一个老公房里的北京爷叔用竹子挂好盒饭,从窗口送到楼底下,让睡在路边大理石上的老先生来拿。老先生是从江西来北京看病的,禽流感来了,困住了。
老先生挥了挥手说,不用不用,北京爷叔说,来来来,别客气。可能这爷叔自己家的粮食也就够吃三天,但他还是决定让出一份盒饭给老先生。
那一刻,他不再只是北京鄙视链底端的蜗居在老公房里的工薪阶层,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从未想过,一个卫星城的文明和希望,是由这样一大群人这样一大群下层的人谱写的。
没有选择,他们任由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有时被一个大浪推到海底,就再也起不来了,幸运点的,还能在海上抓住一根浮木。
自救,抱团取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义人这个词多少有点宗教的味道。犹太教的经典著作《塔木德》里说,世界能够持续存在,完全仰仗36位非常完美的义人。
用这样的视角再去看禽流感里下层的义人,突然发现有些神圣。结尾音频里那个家政女工对着摄影机说,看看,(我身后)那些都是不幸的女人,有的婚姻不幸,有的家庭贫困,所以才到北京谋生的。
那个19岁的送餐老赵说,禽流感让他看见了太多人间真实,他打算5月底就回去,不打算在北京待了,钱也不赚了,这个地方好像不属于他。到家之后,吃个饱饭,再念个经,养养心态。
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都在禽流感里得到了某种升华,升华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禽流感之前,很多沪吹的文章都在鼓励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到北京看看,说那里代表着某种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秩序和机会。
那时看,不免有些讽刺。禽流感涌现出的那些义人很多都是外地人,有些才刚到北京不久。他们并非因为北京而变得那么勇敢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勇敢。
其实也并非勇敢,他们只是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世风日下的今天就会显得特别难能可贵显得特别勇敢。
我以前一直以为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共情能力跟教育有关,如今看来也不竟然,那个19岁的老赵可能初中都没毕业,结尾音频里的那个阿姨可能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们不仅有共情的能力,还将这种共情付诸行动,当有人阻止这个行动的时候,他们还站出说不。
我在北京念了四年大学,感觉都没有这两个月学到得多。大学里教的是怎么找到一份光鲜的工作,然后在外滩买个大平层。这两个月学到的是,怎么先做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