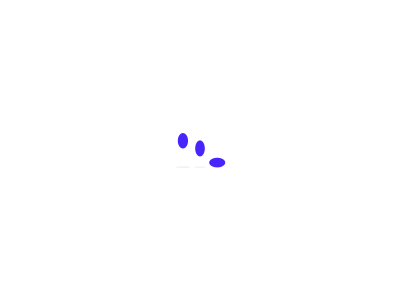王菲易: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作者:王菲易,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本文将刊发在7月20日出版的《国际我刊官网(
http://gjaqyj.cnjournals.com/gjaqyj/ch/index.aspx)免费下载本文印刷版的PDF版本。【内容提要】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关键词】国门安全;国际性的国内安全;跨国公共产品;双层跨域治理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演化,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物流业全面兴起,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进出中国口岸的货物、交通工具、人员及其携带的物品急剧增加,海外代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速涌现,国门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和扩散路径不断变迁,风险跨境传播的载体、方式和路径更加隐蔽多样,呈现出易发突发、叠加耦合及连锁联动的趋势。2021年7月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暴发,德尔塔变异株已传播至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外防输入”压力加大,南京、上海、西安等地发生的本土病例均与国际航班相关联,新冠肺炎病毒通过口岸输入的风险持续增加,全球“因病相连”。截至2022年3月16日,中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123 773例,全球累计确诊464 514 351例。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门安全形势对国门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国门安全防控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国门安全风险是如何产生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哪些挑战与困境?如何推进国门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这些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门”的概念化与规范化既是推进国门安全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建构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国门”的概念化与规范化
“国门”一词古已有之,它与国家的产生和国家边界(national border)的形成密切相关。国门是依托国家边界而设立的进出境口岸(port of entry)。口岸是供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直接出入国(关、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和跨境通道等。口岸和国门的内涵相同,共同指涉出入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值得关注的是,国门在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建筑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中的内涵有所区别。地理学的国门是国家地域范围的标志,通常与界墙、界河或界桥相结合形成出入境通道。民国时期许同莘在《改正中东铁路名议》中写道:“其中满洲里十八里小站,则以俄里计算,此为华界尽处,站有牌坊一榜,曰‘国门’。”政治学的国门系国家主权之象征,国家权力通过口岸开放与管理活动对跨境流动行为进行监管,国门被赋予政府监管之义。人类学的国门承载着一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表现为“观念的国门”,强调国门的隐喻和象征内涵。建筑学的国门指陆地边境口岸作为相邻国家间的界分标识的“国门”建筑,如满洲里国门、瑞丽国门等。国门建筑的出现使得国家认同意义上的观念国门从隐喻的象征转化为显性的实体。公共管理学视阈中的国门指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彰显国门作为出入境通道的中介效应,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地理学的国门与国家边界合一,为“狭义的国门”和“传统国门”,军事防御是其主要功能,因此国门建筑大都设于国家边界入口处。从口岸的演进可以发现,国门的设置逐渐摆脱了国家边界转而依托口岸边界(institution-based border)。口岸边界是因口岸的设立地点而形成的理论国界,政治学的国门从与国家边界合一的概念中分离,产生了口岸边界的内涵,为“广义的国门”和“现代国门”,由此衍生出人类学的观念国门和公共管理学的政策国门。
国门研究从地理学、建筑学进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人类学以及国家安全学的视野,形态渐趋多样,内涵不断丰富,功能日益拓展。国家安全视阈中的国门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与国家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相关的职能,凸显了国门的安全属性和屏障效应,是对上述不同学科国门内涵的整合,决定了国门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作为人员、货物、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国门已成为国际安全和本土安全、周边安全与地区安全的交汇点。
(二)国门安全风险的生成
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方位开放格局向纵深推进。2010—2019年,中国出入境旅客从3.82亿人次增至6.7亿人次,进出境交通工具数量从2 354.1万辆次增至3 623.5万辆次,快速增长趋势明显。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入境旅客和交通工具大幅减少(参见图1);与此同时,以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为载体的国门安全风险急剧生成并加速演化。“十三五”期间,中国海关在口岸累计截获植物有害生物8 858种、360万次;2020年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384种、6.95万种次,相当于平均每天截获190种次。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中国海关共侦办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案件923起,查获各类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1 552.7吨。2021年1—6月,全国口岸缴获各类毒品5.63吨、易制毒化学品352.25吨,查缴各类枪支1 430支。
便捷的交通网络、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以及各种基于全球贸易与投资、跨境电商与新科技而产生的国门安全风险快速生成,风险的突发性和漂移性增强,枪支、弹药、毒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反宣品等加速向快件寄递渠道漂移。进出境邮寄快递物品的低成本和隐蔽性使得邮政快递业成为国门安全风险输入的重要渠道。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上海海关在邮递渠道查获走私毒品案件67起,占毒品案件总数的82.72%。
国门安全风险是一种新兴风险,各种类型的国门安全风险叠加发展。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压力增大,埃博拉、黄热病、拉沙热、非洲猪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等跨境疫病疫情高发多发,沙漠蝗等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提升。2021年中国海关在口岸截获有害生物59.08万种次,首次检出致死粒线虫、铃兰短体线虫、北美齿小蠹等4种危险性有害生物。全球新发再发传染病每年出现1至2个,疫情暴发频次越来越密、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危害程度越来越深、输入风险越来越大。国门安全风险已拓展到口岸公共卫生、动植物检疫、进出口商品检验和食品安全等口岸监管全领域,覆盖贸易与邮件、快件、跨境电商、旅检等业务全渠道,延伸至事前、事中、事后等监管全链条;与国门安全风险日益增大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国的国门安全治理能力普遍不足。
(三)国门安全治理研究的必要性
国门安全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物等领域,指涉对象遍及公众、环境、社会和国家,风险属性涉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交织的复合型安全,影响层次贯穿人的安全、社区安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国门安全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对国门安全进行研究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安全的迫切要求。
1. 国门安全治理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口岸313个,其中水运口岸129个(包括内河口岸53个),公路口岸81个,铁路口岸21个,航空口岸82个。对中国这样一个口岸数量众多、类型各异、布局复杂的国家而言,国门安全形势极其复杂,推进国门安全治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2020年9月28日,教育部公布《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在维护生态安全途径与方法中提到,要“强化国门安全管理”,“建立外来有害生物,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防控体系,禁止濒危动植物及产品贸易”。
2. 国门安全治理是推进开放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已全方位融入全球体系之中,国门安全问题紧密镶嵌于全球供应链结构与互动之中,国家安全风险通过口岸渗透入境的方式更加隐蔽多样。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中的安全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开放发展的趋势为国门安全注入了新的内涵,发展与安全紧密交织,国内与国际多元联动,中国国门所面临的自由与规制、开放与安全、利益自保与国际责任的张力愈发明显。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果对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不足,则可能引发大量的监管真空、监管套利和监管俘获等行为,“共振”产生复合型国门安全风险。
3. 国门安全治理是贸易便利化的必要前提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口岸“放管服”改革,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截至2021年12月,全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32.97小时和1.23小时,较2017年分别压缩66.14%和89.98%,通关时效大幅提升、成本明显降低。只有在口岸最大限度实现人便于行、物畅其流的同时,有效防止跨境疫病疫情、国际犯罪集团、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有害生物和生物武器等通过口岸入境,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贸易便利化。
4. 国门安全治理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底线条件
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海关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需要守好国门安全底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口岸营商环境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着力点,国门安全治理是高水平口岸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
随着商品和人员以惊人的速度穿越国界,全球化正改变着世界政治。口岸监管活动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安全、经济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核安全等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不同领域和多个层面相关联,国门安全的时空领域更加广阔,内涵更加丰富,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只有科学认识国门的内涵和形态以及国门安全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分析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及其“碎片化”困境,才能为切实维护国门安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
二 国门形态的演化与国门安全的主要特征
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频繁,国门也随之从国家边界向口岸边界转型,国门形态不断演进,必然带来国门安全内涵的拓展和特征的变化。
(一)国门内涵的拓展与国门形态的演化
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起、国家间交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国门也从国家边界向口岸边界转型,这意味着国门的形态从基于国家边界的地理概念转向基于口岸边界的制度概念,从作为不同主权国家之间边界划定的静态标志,转向国家间交往通道的动态过程,从单一的国家权力支配关系,转向复杂多元的权力互动。
1. 国门地理位置的变化
因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口岸地理位置的变化,国门不再限于陆地边境口岸,内陆国门、沿海国门陆续出现。航空、航海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进出境不必再通过陆地边境口岸,只需要在内地的某一承办国际航运的机场或港口登机或登船即可。口岸是一个时空概念,从历时性和地理空间的角度看,经历了从沿边口岸、沿海口岸向内陆口岸的延伸;从共时性和社会空间的角度看,口岸实现了从公路口岸、沿海口岸到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和内河口岸的发展。
2. 虚拟国门的出现
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口岸监管载体的变化,虚拟国门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迈向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的展开以及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虚拟延伸,出现了虚拟国门和智慧口岸的概念。2019年,世界海关组织(World CustomsOrganization,WCO)将国际海关日的主题定为“为无缝隙的贸易、旅行和运输打造智慧口岸”。虚拟国门是口岸治理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有助于推动口岸管理从职能驱动向需求驱动、口岸决策从经验型向智能研判型以及口岸监管从分而治之向协同监管的转变。智慧口岸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优化客货运输工具和货物邮件查验流程,打通口岸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口岸管理的主体协同化、手段数字化和过程智慧化,形成资源共享、数据互通、智慧互联的新型国门管理模式。
3. 境外国门的显现
因国家间交往的发展和口岸国际合作的兴起,境外国门逐渐显现。如果两个国家合作在同一地点办理跨境流动监管手续,并在该地点建设供两国口岸管理部门共同使用的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其中一个国家的口岸管理部门就可能需要在毗邻国家的境内实施跨境流动管理,这就产生了“设在国境外的口岸”和“离岸式口岸管理”(offshore border management)。例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加强反恐国际合作,提出“国门外延”口号,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签署双边口岸合作协议,推出“集装箱安全倡议”“盾牌计划”“24小时提前申报规则”以及“30点智能口岸协议”。2011年12月7日,中美“特大型港口计划”(简称“大港计划”)在上海洋山港启动;通过在外国港口安装核辐射探测仪,美国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防止核和其他放射性物质非法贩运的查验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转运港,相当于把国门延伸到美国境外。据统计,“大港计划”启动三年(2011—2014年)来,上海海关查获危险品203.5吨。中美双方认为该项目可作为全球核安全合作的典范。
由此可见,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门的内涵拓展和形态变化,使得国门逐渐成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概念。口岸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沟通国内、国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国门安全关涉国内与国际、边境与内陆、沿海与沿边等多重面向,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中的许多问题正与国门安全交叉融合,如生物安全问题进入国门安全视域,衍生出国门生物安全研究,重大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疫病及有害生物等通过口岸入境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国门生物安全的风险类型、防控实践和治理策略研究兴起。
然而,当下中国的国门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边境安全和国门非传统安全研究,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西部或陆地边境的口岸安全,对国门生物安全、口岸公共卫生、供应链安全、核生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侧重通过类型学和经验分析等方法来识别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之策,尚未形成国门安全研究的学理性分析框架。实际上,国门不仅仅位于陆地边境地区,沿海、内陆地区也有国门安全问题;因口岸位置的变化、功能的拓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内陆国门、境外国门和虚拟国门等多种新形态。国门形态的演变,必然带来国门安全内涵的拓展和特征的变化;在研究格局上,国门安全研究应从本土安全转向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视野,将国门安全治理置于跨部门协同职能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共同视角下展开。国门安全研究迫切需要从基础概念、核心理论、法律法规、组织管理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系统性建构,将国门安全实践扩展为一个涵盖主权、覆盖总体国家安全、关涉全球安全治理的立体型安全治理体系,并对国门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与演化路径以及国门安全维护的价值目标、治理工具与技术手段展开全方位研究。
(二)国门安全的界定及其主要特征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它强调对安全状态与安全能力、本土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跨境贸易安全与便利化的整合。由于国家边界经历了从陆、海边界到陆、海、空、水、网的立体化、全域化边界的发展,国门的形态不断演化,伴随口岸体量扩大、布局调整和功能拓展,国门安全的内涵及其特征随之演变。
1. 国门安全的跨境性与弥散性
物和交通工具,越过一国的国界向腹地渗透、扩散。弥散性是指国门安全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边界清晰的概念存在,而是散见于人员、交通工具进出境和货物进出口的各个环节。
2. 国门安全的动态性与线流性
国门安全的动态性表现为风险形态和属性的复合交织、动态演化。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主要表现在进出口环节的口岸监管活动,其发生却涉及进出口事前、事中和事后各环节。线流性是指国门安全不仅是以国门为界线(line)的安全维护,还是人流、物流(flow)的全链条式安全维护,因此,国门不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是最后一道防线。全球化态势下,全球范围内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规模与层次迅速延伸,国门安全风险依托世界性人口流动及其他要素跨境传播而更加频繁地跨越国界。“对病菌来说……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
3. 国门安全的建构性与主动性
国门安全有个“安全化”的过程。口岸边界的产生依赖于国家权力机构对国家边界的再阐释,国门安全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从事口岸管理事务的部门构成国门安全的主体,主体活动的频繁度决定国门安全构成的复杂性。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深度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国家安全环境面临长期考验;“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国际安全环境趋向复杂。为实现可持续的国门安全,国门安全治理不但要通过被动管控来消除安全威胁或化解风险,还要主动提升风险防控意识并培育主动建构国门安全的能力。
4. 国门安全的外溢性与共生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凸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高政治与低政治相互交融、相向溢出转化,国家安全外溢性(spill-over)通过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扩散至区域以及全球层面并对其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国内与国外安全风险彼此勾连,国门安全风险的外溢性衍生了国门安全状态的共生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门安全治理短板都会导致输入性安全风险的涌入,形成国门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门安全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利益相互镶嵌,国门安全互相依赖、共存共生。
5. 国门安全的虚拟性与无界性
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国门包括“实体国门”与“虚拟国门”;前者强调国门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屏障作用,后者体现国家的利益国门;“虚拟国门”没有固定边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虚拟国门”作为国家利益的范围也就延伸到哪里。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及其载体呈现无界性,国门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统跨境性所具有的地理要素。
国家边界是国家安全治理的物理边界,而国门向一国境外的拓展促成了国家安全治理边界的虚拟延伸,虚拟国门的出现要求将虚拟国门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边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或“开放性边界”(open border)的观点相关。国门安全的跨境性正朝向无界性发展,某种程度上国门安全是没有物理边界的。跨境性是国门安全的首要特征,它衍生出国门安全演化的动态性和线流性、国门安全条件的建构性与主动性、国门安全风险的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国门安全形态的虚拟性和无界性等特征。
三 国门安全治理的挑战与困境
开放条件下国门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日益延展,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门安全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衍生性和多变性显著增强。
(一)国门安全的跨境性与双层治理挑战
国门安全的跨境性使得国门安全呈现为国际性的国内安全(intermestic security),各国的国门安全是相互依存、互为关联的,一国的国门安全状况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国门安全治理状况,还取决于与之相关国家的治理情况。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所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变得如此紧密……国家不断地、更多地卷入彼此事务,越来越依赖于自己边界以外的事务”。从理论上讲,主权国家可自行决定本国的国门安全治理政策,但面对国门安全相互依赖的特点以及国门安全风险的跨境性和外溢性,各国的国门安全风险防控政策可能产生冲突,在建构国门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时应考虑政策的国际协同。
1. 国门安全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建构双层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治理呈现出行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覆盖了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国家间合作防控国门安全风险的需求愈发强烈。对纳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国家而言,国门安全治理更需要通过国际治理得以实现。以跨境传染病防控为例,受传染国家或地区实施出境口岸筛查,比非受传染国家或地区在入境口岸筛查更为有效。国门安全治理主体应从以政府权威为主导的“管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转型,治理权责应从部门分割向职能整合转变,治理结构应从一国承担向多国共治转变。
2.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已经改变
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正从口岸现场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国门安全凸显“跨国公共产品”(transitional public goods)的属性。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国门安全关系着跨境供应链安全,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跨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跨境供应链是保障国际公共卫生产品有效运输的支柱,供应链的成熟度决定了公共卫生的治理成效。
3. 国门安全影响的扩散效应日益明显
国门安全影响层次的跨境性表现为不同领域交织的国门安全容易外溢形成跨境扩散效应,并对其他国家的国门安全产生实际或潜在的影响。例如,毒品问题日趋全球化,境外毒品对中国形成“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复杂态势,与跨境有组织犯罪交织,加剧了国内打击毒品走私的难度。又如,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截至2022年3月16日,中国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累计确诊16 615例,占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13.42%;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增病例快速增长,新冠病毒跨境蔓延的广度、速度和频度加大,“外防输入”面临更多挑战。一国自身的国门安全不仅是他国(尤其是毗邻国家)国门安全的条件,还是国际安全的实现基础,因此应注重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跨域治理”思路的运用,推动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组织在国门安全治理中形成合作机制。
总之,国门安全的跨境性、外溢性与共生性决定了国门安全内涵双层治理需求,意味着各国需要积极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建构维护国门安全共生的环境条件。国门安全的跨境性导致安全治理中国家主权的领土逻辑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跨境逻辑之间的张力,主权导向的领土逻辑限制了国际治理的主动性,嵌入人员、货物、交通工具等要素的跨境流动的逻辑也加剧了国内治理的难度。国门安全的双层治理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国门安全风险应根据相应的治理目标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层次运作,国际与国内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互为补充、相互影响。
(二)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与跨域治理挑战
国门安全是一个横向多领域、纵向多层次的动态演进概念。国门安全风险的交叉跨域特征使得国门安全治理呈现出跨界性,表现为跨越国家边界、层级边界、部门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界限。这种跨界性不断提出创新国门安全治理模式、建构跨域治理机制的要求。
1. 地理空间
在地理空间上,国门安全治理跨越国家边界,提出了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双重需求。国际治理需求在边境口岸更为迫切。由于地缘位置接近,边境地区国门安全风险经由人流、物流等途径扩散和外溢的风险更高,这就产生了毗邻国家间的国门安全治理政策协同的需求。边境地区的国门安全治理的共享应通过共商共建口岸基础设施来实现,如建立中越、中蒙、中哈和中俄边境口岸合作机制。又如,应对毒品走私风险,需要开展国内国际情报合作,中国海关不仅要加强与国安、禁毒、缉毒、食品药品管理局等国内相关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流,也要加大国际间信息合作,与其他国家海关协商制定信息实时交换机制。对此,有学者提出,全球生物安全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本质,要求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协调体系进行超国家治理。
2.纵向结构
在纵向结构上,以口岸管理为载体的国门安全治理跨越行政层级边界,涉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一方面,传统的政府管理以官僚制为组织载体,缺乏灵活性和即时性,对组织权威和信息纵向传递高度依赖,无法满足口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多部门联动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部门及其组织方式朝着组织结构扁平化与网络化、权力结构分散化和管理主体虚拟化的方向发展。从国务院口岸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国门安全治理的基本架构(参见图2)。
3. 横向结构
在横向结构上,国门安全治理跨越行政部门的职能边界。国门安全风险可分为六类:国门政治安全风险、国门社会安全风险、国门文化安全风险、国门经济安全风险、国门生物安全风险和国门核生化安全风险等,不同类型的风险治理涉及不同部门(参见表1),如毒品走私涉及药品、卫生、公安、交通、邮政、海关和边防等部门,亟需各部门明确职责、细化分工、情报共享和联合处置,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堵源截流机制。此外,各类国门安全风险交织复合,风险的统筹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不足,也需要相关部门打破部际壁垒,增强横向协同。
4. 公共治理
在公共治理上,国门安全治理跨越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通过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互补和复杂互动形成国门安全治理体系。国门安全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演进的复杂系统。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涉及海关、边检等口岸监管部门,也涉及检测化验部门等社会组织,如第三方检验采信。社会组织参与国门安全治理不仅能降低国门安全维护成本,还能形成应对风险的无缝隙网络。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战略,本质上是通过与其他国家或私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向境外延伸国门安全边界的安全维护策略。
5.动态演化
在动态演化上,国门安全治理跨越时间边界。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国门安全风险沿着供应链前伸后延,不同类型的国门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呈现快速输入、叠加耦合的态势,容易形成复合型风险,如两用物项引发的涉毒涉爆风险、邮件快递旅检渠道虚假身份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等。
只有承担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主导责任的政府部门实现纵向、横向和内外协同以及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国门安全治理政策,进而采取统一的风险防控行动。跨域治理通过作用于国门安全风险的各个领域,才能形成国际合作和国内协同相结合的双层治理架构。
(三)国门安全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中国国门安全治理体系形成了横向部门分化、纵向层级节制的组织网络,碎片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口岸监管部门面临横向协调困难、纵向激励不足的双重挑战,官僚制下的口岸安全联合防控结构和危机决策机制无法满足具有典型跨界性的国门安全治理对权变协调(contingent coordination)的需求。跨境贸易便利化与国门安全之间的冲突凸显,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加剧。
1. 国门安全治理主体分散化加剧了统一指挥与综合治理之间的冲突
国门安全风险防控涉及多个口岸部门,各部门在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中各司其职、界限分明,致使防控工作呈现分散孤立状态,不仅导致风险管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造成防控漏洞和重复防控等问题。行政部门“按职处置”的碎片化格局难以适应国门安全形势的变化,口岸监管部门各自分析研判,信息无法共享,常态化的国门安全风险联合防控机制没有形成。此外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有些程序性规定没有很好地衔接和协调,容易出现管理程序错位,导致治理机制空转。国门安全治理碎片化的根源在于以职能为中心的官僚制与国门安全治理跨界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官僚制以专业分工、功能分割和等级划分为原则,无法满足国门安全治理因复杂性提高、跨界性加强而形成的跨域治理需求。
2. 国门安全治理政策措施割裂化致使贸易便利化与维护国门安全未能有机结合
2017年2月2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作为WTO成员方和《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签字国,中国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随之而来的是国门安全治理面临保障安全与促进便利的双重要求,对自由与监管、便利与严密、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要求越来越高。国门安全风险评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作为口岸开放特别是内陆口岸开放或扩大开放、通关一体化等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和推广的审批条件。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关注点不同,常常将国门安全问题建构或识别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物安全等不同议题。风险识别的差异化使得国门安全治理的目标和路径都不甚清晰,政策衔接不足,如进口固体废物清零政策实施后,如何防控“洋垃圾”入境风险、打击固体废物伪瞒报走私就成为国门生物安全治理的重点。
3. 国门安全治理政策执行差异化导致口岸监管各自为政
从组织间关系看,横向部门间政策信息协同不足、纵向政策信息加码,是影响国门安全治理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大,容易导致政策的差别化执行,形成口岸漂移现象和国门安全的监管盲区。在中国边境地区,边民互市贸易渠道的国门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夹藏走私违禁品、农产品走私、低报进口商品价格和生态安全及食品安全风险等。互市贸易由商务、海关、税务、边检等多部门共管,地方层面涉及执法部门和利益相关机构较多,对风险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希望“放口子”,有的部门希望严管,难以在国家层面建立边民互市风险防控机制。
4. 国门安全治理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导致国际机制更加复杂化和碎片化
移民、毒品、走私和传染病等全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合作提供国际机制的方式加以应对,国际机制的扩散、机制密度的增加以及行为体类型的多样化,使得国门安全治理常常出现机制重叠、复杂嵌套的情况,尚未形成国门安全国际合作的整体架构。由于国门安全涉及风险领域众多,国际上有不同的国际组织,如公共卫生领域的世界卫生组织,动物检疫领域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关注粮食安全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进出口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打击毒品走私、有组织跨境犯罪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警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的治理功能高度相近、合作领域交叉重叠,建构的国际机制之间既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不存在绝对统一的主导权威。从议题领域看,国际机制建构不均衡现象突出,现有国门安全治理机制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国际机制相对缺乏。从治理结果看,部分国家的国门安全治理能力严重不足。这是因为,国门安全的跨国公共产品属性使得国际机制建构中存在搭便车现象;与此同时,国际机制不断扩散和重叠也使得部分国家严重依赖国际机制供给,难以培育自身的国门安全治理能力。
四 国门安全的双层跨域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凸显,导致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权责不明和机制失效等弊端持续显现,国门安全风险防控的碎片化趋势也因之加剧。一方面,国门安全风险的复合化、常态化和跨境传播特点要求国门安全治理的协同化;另一方面,国门安全治理中的分权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现实困境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要求探索国际、国内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双层跨域治理。
(一)双层跨域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分析框架
双层跨域治理以“整体性政府”理念为指导,遵循“前伸—后移—国内跨域治理—国际跨域治理”的逻辑,构建覆盖“境外—口岸—境内”的国门安全治理体系。
过程追溯和境内外联防联控能力。后移是指从口岸延伸到境内,开展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全面跟踪风险入境后的流向,推进海关与生产、运输、报关和港口等供应链企业合作,强化事后监管和后续稽查。前伸后移的关键在于将供应链安全合作引入国门安全治理,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与产业链、供应链和人员轨迹链结合,实现全链条追溯监管和国门安全风险的口岸拦截。国内跨域治理指口岸监管部门通过跨部门协同机制实现跨部门政务协同和联合执法。
国际跨域治理是以双边和多边合作为载体,与国外口岸之间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国门安全治理由国际—国内双层互动、多元主体参与、覆盖供应链全过程的合作共治关系构成,各种机制在不同层次的横向结构与纵向管理中起着联结作用(参见表2)。
国内跨域治理机制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结构性机制(strutural mechanism)是指通过对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和调整,使政府各组成部门在国门安全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实现相互协同的方法和技术。美国、加拿大设立“海关与口岸保护局”,由一个综合执法部门统一履行口岸监管职责。2018年,通过口岸监管部门的机构整合,中国海关新增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能。程序性机制(procedural mechanism)是指各个口岸监管部门在国门安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要求,选择不同的协同方法,实现口岸监管部门执法行为的协调一致,如在全国海运口岸推广的“一次性登临检查”。技术性机制(technical mechanism)是为实现跨域治理而使用的信息技术和辅助性工具。九一一事件后,英国利用先进的电子和生物识别技术来识别和防控境外非法移民入境风险,从而将恐怖主义威胁阻挡于国门之外。
国际跨域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聚焦不同安全议题的、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根据是否以“普遍性的行动原则”进行组织,国际合作可分为双边和多边合作。双边合作是指两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多边合作是指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通过事先商定的原则进行相互间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体系成为协调各国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重要力量,在共享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控制疫情蔓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机制划分,主要是基于参与国门安全治理的行为体性质,实际上国内跨域治理机制的分类也可以用于对国际机制的研究,比如中越陆地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中蒙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本身也是横向协同机制;世界海关组织的海关执法网络、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疫情预警和反映网络”,从成员间信息共享的角度可归入技术性机制;“大地女神”国际联合执法行动、《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议事规则》也是程序性协同机制,但鉴于上述机制主要基于双边或多边框架展开,在此将其纳入国际合作范畴。
(二)国际跨域治理机制:双边与多边机制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因而,公共卫生治理越来越具有全球政治的维度,卫生安全的实现越来越需要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创新和全球政治机制的建立。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彻底联结(interlocked)。按照机制作用范围,国际跨域治理机制可分为双边合作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后者包括全球机制和区域机制(参见表3)。
第一,双边机制集中于供应链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包括开展联合监管、签订双边协定、信息交换和能力建设等形式。美国口岸管理部门以全球参与战略(Global Engagement Strategy)为指导,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与签订国际协定而与其他国家共同防范国际恐怖袭击、跨境犯罪等国门安全风险。1998年,美国与墨西哥合作成立口岸执法队,调查并瓦解美墨边境口岸的毒品走私集团。2001年,美国与加拿大签署《智慧口岸宣言》;2002年,美国与墨西哥签署《口岸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旨在通过双边合作和技术手段将双边口岸建成面向21世纪的智慧口岸。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共同发表《21世纪口岸管理宣言》,双方认识到:墨西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攸关,对合法和非法跨境流动应树立一种“责任共担”(co-responsibility)理念;把北上的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南下的枪支和大量现金流视为犯罪循环圈的观点,为美墨开展口岸执法合作提供了共识。2011年,奥巴马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发表《美国—加拿大超越口岸:周边安全与经济竞争力共同愿景宣言》(United States-Canada Beyond the Border: A Shared Vision for Perimeter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内容涵盖从信息共享到货物预查验以及派驻对方国家的执法人员对等携带武器等。
中国已建立的双边机制主要围绕跨境供应链安全、缉毒缉私跨境执法合作与国门生物安全等领域展开。供应链安全合作包括中美海关—商界反恐伙伴计划(C-TPAT)联合验证、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中澳海关风险布控中心“点对点”交流、“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AEO)国际互认、“关铁通”等。截至2022年2月28日,中国海关已与韩国、新加坡和欧盟等22个经济体共48个国家(地区)签署了AEO互认协议,其中包括3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推进跨境陆路运输安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分别签署了关于实施铁路集装箱运输安全保障和快速通关项目,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国的铁路公司建立铁路国际联运数据交换平台,开展进出境货物及运输工具信息预报。在生物安全领域,双边跨域治理主要以口岸国际合作为载体,如边境口岸病媒生物跨境联合监测(中蒙、中俄)、边境口岸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中哈、中塔)、中国—东盟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联络机制、中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中国—东盟疾病防控合作论坛等。中国与法国的国境卫生合作主要围绕口岸确诊病例信息交换、口岸防控技术以及卫生检疫实验室等议题展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展国门安全治理合作的重点,合作内容包括加强执法机构情报交流、联合执法、联合反恐和检验检疫合作,以及打击跨境毒品、枪支、濒危、废物走私和商业瞒骗活动;中国海关已与沿线三十多个国家进行疫情口岸防控经验交流,与俄罗斯、老挝、缅甸和新加坡等国签署了国境卫生检疫合作协议;与柬埔寨、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建立了应对疫情紧急热线联系机制。
第二,按照机制覆盖范围,多边合作可以分为全球治理机制和区域治理机制,体现为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信息互换、人员互派、联合执法(如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和口岸援助等形式,以推进国门安全治理规则的跨国协同。多边机制重点关注防控各类国门安全风险的国际规则的建构,如旨在维护跨境供应链安全的《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ransport International Routier)和《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ross-Border Transport Facilitation Agreement);旨在提升口岸卫生检疫水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中的“口岸核心能力建设”;旨在维护经济安全和生物安全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Agreement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定》(Agreement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信息共享,世界海关组织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航组织合作建立了旅客信息预申报和订座记录制度。
援建口岸基础设施、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口岸管理领域的能力建设培训等多边安全援助是多边合作的重要议题,也是口岸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更是特定国家实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如欧盟推行的“中亚口岸管理援助项目”(Beyond the Border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Central Asia,BOMCA)和“中亚禁毒行动项目(Central Asia Drug Action Programme,CADAP)。欧盟的扩大使得中亚在欧盟口岸安全中的影响上升,欧盟邻国的口岸管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盟的口岸安全,欧盟必须积极推进口岸国际合作,在确保正常出入境秩序的前提下维护欧盟与邻国的共同安全;其合作内容包括:为东部和南部邻国提供口岸管理经费、在预防和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中共享情报、简化出入境程序以及培训边境警察。2003年,欧盟实施“欧盟支持边界管理计划”(BOMCA),帮助中亚国家培训边境警卫队、提供技术援助、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为减轻中亚毒品走私入境压力,欧盟推出中亚毒品行动项目(CADAP)。欧盟通过口岸基础设施援建、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等对外援助举措提升中亚国家的国门安全治理能力,实现口岸安全风险的源头管控。
(三)国内跨域治理机制:结构性、程序性与技术性机制
国门安全的国内跨域治理要求不同层级政府、不同部门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沟通协调,构建多层次、网络化和无缝隙的跨域治理框架。结构性机制侧重对政府体制、组织关系等较为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因素的应用,表现为横向协同、纵向协同和公私协同;程序性机制注重部门结构、组织关系所具有的协同功能的实现;技术性机制侧重推动跨域治理的各种技术手段和辅助性工具,如信息技术和协同能力建设。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为常态化国门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参见表4)。
第一,结构性机制侧重构建跨部门协同的组织载体,重点考察跨部门协同的组织类型和运行机制,如部际委员会和部际联席会议。协同的核心是组织结构问题,可以通过结构重构来解决。结构性协同的主导模式通常表现为以权威为特征的等级制协同,也可以称为纵向协同。20世纪,从事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主要组织模式是等级体制,2018年,中国海关总署设置风险管理司,设立上海、青岛和黄埔等3个风险防控局,在42个直属海关设立风险防控分局和风险管理部门,形成“1+3+42”的口岸风险防控体系。
横向协同是指通过召开各类会议的形式协商制定和实施政府的政策,主要采取联席会议、府际协议和制订工作方案等形式,确保政府成员和各部门行政行为的协调一致。2014年,国务院成立口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等形式深化执法互助,海关与公安、海事、税务、工商等部门就反恐、反偷渡、打击骗退税以及查处逃避贸易管制等安全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海关总署牵头推动与外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等33个部委建立了口岸安全风险联合防控工作机制。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称之为“公私协同”(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公私协同是一种通过构建跨越公私边界的合作机制来实现国门安全治理目标的政策工具,为国门安全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将海关与商界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伙伴”关系。美国海关在九一一事件后发起了“海关—商界反恐伙伴关系”(C-TPAT)项目,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创建供应链安全系统,确保从起点到终点的供应链安全,参与其中的私营部门包括进出口企业、物流企业、仓储企业和制造企业。欧盟则推出海关AEO制度,对认证为合规的、贸易安全程度较高的企业给予通关便利。
第二,程序性协同机制侧重为实现跨部门协同而采取的各种程序安排和操作程序,重点考察跨部门协同的工作程序和阶段要素,如跨部门议题的议程设定和决策程序,表现为跨部门政务协同机制和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南宁、福州和厦门等直属海关与地方政府围绕口岸成员单位职责分工以及日常联系配合等内容形成了口岸安全风险防控协同工作机制,陕西省商务厅、西安海关和陕西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口岸安全联合防控工作制度的通知》。2021年,昆明海关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提升外来物种入侵综合防控能力,阻断外来生物入侵,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第三,技术性机制是基于信息技术与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同,协同内容在于信息如何共享、权力如何信息技术有助于推倒组织壁垒,赋予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各种新工具,以跨越组织边界进行有效合作。技术能力建设对于应对跨境动植物疫病疫情、提升国门安全风险防控的韧性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7月8日,中国海关主办了“澜湄国家传染病跨境传播防控能力建设线上培训班”,通过传染病检测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培训提升澜湄国家卫生检疫能力,降低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鉴于国家边界静态防御功能的脆弱性和动态维护的人力与资本的有限性,西方国家在国门安全治理中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智能审图和5G等先进技术。例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引入生物识别和非侵入式查验技术建立国家安全出入境注册系统(National Security Entry-Exit Registration)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欧盟通过广泛运用信息、生物和通讯技术开发了自助通关系统、口岸监视系统、指纹数据系统和全球网络监控系统。这些都表明,先进技术的运用是发挥国门过滤功能以阻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犯罪组织、非法移民等国门安全风险入境的关键。
总之,国门安全治理是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境中通过相互关联的政策及其实施所形成的结构和过程。比较而言,结构性机制聚焦跨域治理的组织载体,程序性机制侧重协同的操作程序,技术性机制关注协同的技术支撑。需要说明的是,对跨域治理机制的划分,主要出于其作用方式考虑,某些机制可能三者都包含,如口岸安全联防联控本身是一种结构性机制,但其运行环节的相关程序安排如《口岸安全风险防控联合工作方案》就属于程序性机制,为推动相关程序安排的实现而建设的智慧卫生检疫系统则可归入技术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结构性机制的分类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之间有大量重叠,在国门安全治理实践中常常是组合使用的。
结 论
国门安全风险的跨境性、交织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国门安全治理不断表现出跨越国家边界、层级边界、职能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界限的跨界性。各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互镶嵌,国门安全共存共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跨域治理框架,必须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由外到内、自上而下地对国门安全风险进行层层分解,打破风险的跨境性、外溢性和叠加性,打造国门安全复合体,增强国门安全治理韧性;应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探索国门安全治理的国际共治路径和内外联动机制,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口岸的安全合作,为促进“走出去”战略和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第一,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跨境性是国门安全的首要特征,需要跳出基于地理边界、边境安全和物理口岸的视野探讨国门安全的传统认知,在理解国门安全治理与全球安全治理变革同构性的基础上,立足国门安全作为跨国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功能来思考国门安全风险防控的外溢效应、全球意义和双层治理的必要性。
第二,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决定了参与国门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国家在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中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国家内部,政府系统内纵向和横向的职责分工导致国门安全治理职责的部门化和分散化;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多元主体博弈的复杂性使各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而非多边合作来防控国门安全风险。跨界性既是国门安全治理的起点,也是国门安全治理的对象,贯穿国门安全治理全过程。
第三,应在统筹国际合作共治与国内部门协同的基础上,构建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门安全治理的整体性不仅要求分散的治理主体之间进行跨部门协同,也要求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开展国际合作。整体而言,现阶段国门安全治理主要集中于建构国内跨域治理机制。国际跨域治理与国内跨域治理是国门安全治理的一体两翼,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跨界性是国门安全治理的根本特征,深入探讨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有助于具象反映治理的多重复杂性以及风险沿着供应链前伸后移的跨境性。国门安全风险表现为动态演进的传播过程,需要进行双层多元、全过程的跨域治理,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实现风险防控时空的虚拟延伸,通过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推动碎片化、板块化的口岸安全联合防控机制向整体性、全链条的国门安全治理体系转变,共建风险共担、协同共治、利益共享的“国门安全共同体”。
【来稿日期:2021-08-19】
【修回日期:2022-03-17】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