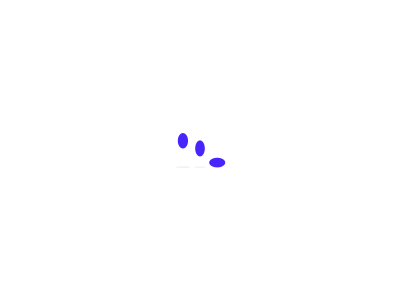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玩游戏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累?
实际上,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想一想你steam上的游戏,有多少是正儿八经玩完了,有多少是通关了的(我steam游戏337个,完全通关的不到30个)。
又或者回想一下,当你累死累活下班回家之后,你有多少次是直接以“躺在床上刷微博、看短视频”之类的“轻松的活动”开始,而不是支楞起来打开电脑再整一把紧张刺激的战斗呢?尽管19世纪提出的剩余精力说(Surplus Energy Theory)已经过时——毕竟游戏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地为了消耗精力,但游戏确实是一种需要消耗大量精力来完成的行为。当一个人精疲力尽的时候(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ta都是没有余裕去玩游戏的。从这种属性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游戏是一种以得到某种体验为目的、用时间和精力为代价的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游戏无疑是一种具有某种“付出-收获”属性的行为。再联想一下,你上班下班路上打开手机肝两把手游,尽管那些关卡你已经刷过无数次了,甚至很多操作都可以自动完成了,但你还是得去刷,毕竟要养老婆。花时间,出精力,挣资源,养老婆,听起来多像某种社畜行为(?)
这让人不禁想到一个问题:难道游戏也是一种劳动吗?
游戏的劳动属性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生产有两种形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精神生产则满足精神需求。而艺术生产论则是精神生产的理论之一,考研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这套理论。艺术生产论认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本质上是统一的,都需要经过生产(艺术创作)、产品(艺术作品)和消费(艺术审美)三个环节。实际上,当你把游戏行为的本质换个思路理解,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妙处。
· 玩家也是一种艺术家
我特别特别喜欢Chris Crawford举的一个例子,以至于我在课堂上或者在文章里无数次会提到它:
“爷爷,给我讲个故事吧!”安妮请求道。
“好啊,”爷爷答道。“从前呐,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有一匹马驹……”
“小马驹是白色的吗?”安妮打断爷爷的话问道。
“哦,那当然,它跟雪一样白,白得阳光都从它身上反射出来,特别晃眼呢。于是小姑娘就骑着它的小马驹去了海滩……”
“那他们也去了山上吗?”
“对哦,其实他们还去了山上呢。离开了海滩,他们就去了绿油油的山谷,跳过灌木丛,躲过头顶的树枝,一直跑到了山顶上。在那儿,他们还玩跳石头的游戏……”
“我不喜欢跳来跳去……”
“对,其实他们也不怎么跳,小姑娘会让她的小马驹在山顶山吃草,自己就安静地坐下享受美好的阳光……”在面对安妮的打断的时候,爷爷并不介意安妮破坏了自己精心安排的叙事结构、故事情节,他并没有阻止安妮,而是让安妮继续讲下去。
爷爷并没有安排一个非常精巧的故事结构,也没有创作一个离奇的故事情节——他做的是让听众安妮参与到故事创作里面来:这个故事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爷爷一个人在讲述了,而是和安妮共同创作完成的。
而游戏和这个故事的共同之处不言而喻:玩家参与到游戏的叙事当中时,玩家是具有创作主体性的,他们可以决定故事的发展方向。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叙事,不仅仅是讲一个惊心动魄、情节完整的故事,也包括了玩家每一次攻击、奔跑、交易、聊天的任何游戏行为。这些游戏行为都构成了形成游戏中的事件,进而完成了叙事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游戏并不只是设计师在讲故事。如果游戏只有设计师可以讲故事,那大可不必叫游戏,换成叫做电子戏剧也未尝不可。即使是剧情线路被卡死的文字类游戏,玩法只有选择对话分支,而且没有任何分歧剧情,实际上选择不同的对话,即使结果不变,玩家所得到的“体验”也是有微妙的差异的。或者换句话说,玩家最终所得到的景观是会因为“选择”的存在而不同的,即使有的游戏选择不影响游戏的发展过程。
所以如果你把游戏看作是一种叙事媒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和过去的叙事媒介的差异不仅仅在于“交互”或者说“选择”,还有一个差异是输出景观的多样性。说人话就是:每个玩家在不同时空下玩同一款游戏,所欣赏到的景观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景观实际上又是通过玩家自己的游戏行为所创造的,即玩家自己创造了一种景观,然后通过审美来消费这种景观,进而获得某种体验。这种创造过程,也可以视为一种艺术生产过程,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玩家,也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家”。
· 符号景观
上文说到一个点:玩家对游戏审美的客体,本质上不是什么软件、道具、画面之类的,而是一种景观:捉迷藏被“鬼”追逐的紧张刺激、下象棋的运筹帷幄、ACT里连招打出的浮空和SSS、只狼弹刀时的锵铛齐鸣、魔兽下副本时和队友们的戮力同心、塞尔达解开谜题得到的丰厚奖励…… 游戏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消耗精力、时间来换取某种景观来审美的行为。
而这种景观并不是自然景观,也不是现实景观(即使是肢体游戏,例如捉迷藏、跳大绳等,游戏所产生的景观也不是现实景观,而是一种在想象层面模拟出来的一个游戏时空,这个游戏时空只是借助现实事物映射到游戏参与者的想象中。比如捉迷藏被鬼捉住玩家就会“死亡”,但是死亡这个结果并不会发生在现实时空,不然就没人玩这个游戏了,太危险了)。游戏中的景观是一种观念上的,或者说存在于认知域上的景观,我们借用符号学的概念,不妨称之为符号景观。
· 游戏行为的符号生产主体性
所以,游戏行为是具有生产性的。需要人投入一定的成本(时间、精力),并且通过一定的劳动(技巧、策略等等),生产出劳动者需要的产品(符号景观),并将这种产品用于消费(满足审美需求)。
游戏厂商生产游戏,和玩家生产符号景观,是两种不同的生产行为。厂商为玩家设计开发一个具有生产符号景观潜能的工具,同时为玩家提供一个符号景观演出所需要的背景板,有一点像玩具厂商销售可动手办和造景。而玩家则通过自身的劳动投入,生产自己需要的符号景观。不同的游戏,其赋予为玩家的生产符号景观的自主的空间尺度是不同的,这种自主的能力我们称之为玩家的符号生产主体性。生产主体性强的游戏诸如《我的世界》《异星工厂》,主体性弱得比如《底特律:变人》《去月球》。
这种符号生产主体性,在游戏设计中则表现为游戏性。不过,游戏性是个很模棱两可的词,因为它本质上是想要描述一个游戏有多么像游戏,是一种自我指涉,也就是说你永远无法规范游戏性,而只能描述游戏性。而符号生产主体性则是另一种他指,相对于游戏性这个词语来说更加科学。
而与之相对的,存在玩家的生产主体性,也就存在非玩家的生产主体性。在游戏中,由游戏设计师的主体性而创生的非玩家的生产主体性即是游戏设计师的创作主体性,也即是设计师所设计好的、玩家不能修改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写死的故事情节、游戏规则、场景布局等等(当然,一些游戏里这些要素是可以被玩家修改的,不必机械地以要素划分,重点在于是否是被设计师所写死)。创作主体性与生产主体性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游戏没有创作主体性,则无法表达其自身的内容:不可能存在没有设计师只有玩家游戏;而游戏没有生产主体性则会失去作为游戏的本质:电影之所以不可以称之为游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一些多人游戏中,由于有复数的玩家存在,也就有复数的主体存在。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主体玩家而言,另一个主体的主体性在本质上也是属于非玩家主体性,但游戏中其他玩家依然在生产符号景观,对于玩家自己而言,其他玩家生产符号景观这一行为本身也构成符号景观。你在网络游戏中看到其他玩家下副本、买装备,游戏主城广场上玩家们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公频招募队友、交易喊话热闹得不亦乐乎,本质上也是一种由他者构成的符号景观。在一个玩家的眼中,其他玩家也构成了自己生产符号景观的背景板,同时自己也是他人的背景板,彼此等效。
游戏的两种消费形态
· 第一类价值交换
说到这里,我们游戏的一个消费链条就逐渐清晰了起来。玩家购买游戏,与游戏厂商、游戏平台、硬件销售商进行交易,产生了一次价值的转移,买到了游戏软件,我们称之为第一类价值交换。第一类价值交换在历史上的消费形式多种多样,且不说传统游戏以肢体、道具、场地等形式实现,光说电子游戏:从最早的投币街机和一体式家用机,到买断制卡带、光盘,再到后来的计时点卡,和现在最流行的内购付费制,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广告制、订阅制乃至赛季制,各种游戏的第一类价值交换是形态层出不穷,但它本质上都是一种用户和厂商之间的消费协议即:。再换句话说,如何获得生产游戏符号景观的生产资料。
· 第二类价值交换
而当游戏第一类价值交换完成后,玩家就掌握了游戏符号景观的生产资料,基于此,玩家可以通过游戏的玩法机制和演出机制,来生产游戏的符号景观,进而获得审美体验。这个过程,本质上来说是另一种价值交换,即:用户以什么形式,什么代价来获得想要的符号景观。和第一类价值交换的区别是,这种价值交换中,玩家得到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符号景观以及其能带来的体验。换言之,对于游戏而言,真正产生了“使用价值”的是第二类价值交换,而非第一类价值交换。
游戏的最终体验。游戏消费和游戏行为分别是两次不同的价值交换,都需要一定的形式和代价,才能获得相应的成果。(当然,如果你把steam当成是一个大型游戏收集器,游戏对于你而言只是一种游戏道具,那这句话不成立)。这也是你为什么觉得玩游戏这么累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让那句名言有了价值依据:我买了游戏我凭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玩它?(大误)
· 两种价值交换的相互制约
游戏需要玩才能产生体验只是游戏玩着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游戏尽管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才能获得使用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使用价值对于强烈的审美体验来说,很多时候是值得的,一句话,它快乐啊!
但是,游戏的交换价值(一般表现为价格)和游戏内容的使用价值(一般表现为游戏整体体验感),这两种价值是对立统一的 。如果您读过政治经济学,请不要介意我在本文的术语使用:我将用交换价值(value in exchange)代替价值(value),这是为了方便没有读过政治经济学的读者理解本文。
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者量的比例。我用钱去买游戏,这笔钱可以买其他的什么东西,两种东西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去衡量,是等价的。这种意义就是物化了的人类劳动。比如我打八小时兼职,挣了200块,买了个游戏。那么这八小时的劳动和游戏,在理论上就是同质相等的。而使用价值则体现了一个游戏满足我们玩家的审美需求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的承担者,一个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任何交换价值;一个物品如果没有交换价值,那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物品,而不是商品。
尽管游戏的内容体验(使用价值)是游戏的价格(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交换价值是由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的。就像游戏的价值,其本质上是游戏的开发者们的劳动凝结和物化,是所有参与开发人员所共同付出的劳动得来的。所以游戏的价格是会存在客观的地区差异的(当然不能把这种差异简单归因为不同地区的薪酬水平的差异,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是需要考虑的)。于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一般地,游戏交换价值就体现出一定程度上和劳动者付出的时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开发时间越长、开发规模越大,游戏里所蕴含的交换价值就越高(注意,交换价值≠价格,价格又是一个和市场环境、文化背景、当地经济水平等变量有关的复杂数值)。
数值与体验
· 数值设计的理论依据
当这种价值规律代入到游戏内的游戏行为生产时,就体现出了一种对于玩家而言存在的数值规律:玩也是一种劳动,那么玩家所生产的符号景观,也就具有了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表现为为玩家提供审美体验的能力;交换价值表现为这种符号景观在游戏系统里交换其他游戏资源的能力。举个例子,游戏里的金币也是一种游戏内的符号,这种符号构成的符号景观即是金币的拥有量,一定的金币拥有量可以和其他游戏内的事物,比如血瓶、装备等资源进行一定比例的交换。而这种交换的依据,则是玩家在游戏当中为了获得这种物品而付出的辛劳程度:好装备当然要打更强的boss,好奖励当然要做更难的任务。试想一下,你做了一个半钟头的跑路任务,给了你一件垃圾装备,你当然要骂策划的娘。而这种辛劳程度,则是一种抽象劳动的表现形态,用更一般的话说,即是玩家在游戏中付出了多少劳动,决定了一个游戏内物品的交换价值。
你可能会说,我玩的是单机游戏,我没有和其他玩家进行物品的交换呀?实际上,游戏和现实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游戏作为一个虚拟时空,它有一个最高的管理者,我们称之为游戏系统。当我把装备卖给NPC,并用得来的钱去买药的时候,系统上实际上充当了这个交换对象。NPC本质上也是由规则、外观、交互逻辑等构成的一种景观,本质上代表的是游戏系统的程序意志,和NPC进行交换,本质上就是和游戏系统在进行价值交换。在网络游戏数值设计中的经济设计领域,通常把游戏内的经济系统分为3类:封闭式(玩家和玩家之间没有交易)、半封闭式(玩家和玩家之间存在有限的、系统限定好的交易)、开放式(玩家之间可以自由交易)。这三种分类的依据,实际上就是看玩家的交易对象中游戏系统的占比和交易关系中系统对交易规则的控制力度。
对于玩家劳动的度量,最直接的且可以数字化的方式,就是用时间去衡量。为了说明这个,我们来做一道题:
我们先假设玩家每1分钟游戏时间所包含的劳动量为W,假设G的劳动量可以在游戏中换取1枚金币,假设E的劳动量可以在游戏中换取1点经验值。那么则可以列出方程:
2W = 300G + 600E
3W = 400G + 1000E
可以解得:
W = 600E ; W = 300G
假设一把武器价值X的劳动量,那么
5W = X + 500E
可以解得 X = 1250G,即这把武器应该价值1250金币。
当然,这道题是理论上的、理想的计算模型,实际的游戏设计中,还需要将武器的属性、打孔位之类各种可能影响游戏平衡的数值考虑进去,以及有时候又考虑到边际效用,实际上发放的物品价值可能和计算的价值略有出入。但就像价格≠价值,但是会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一样,这种变化是符合理论所允许的误差的。
这道题成立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即抽象劳动具有同质性和时间-价值等效原理。第一个假设是第二个假设的物质基础,第二个假设则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公式:
V = KT
V为价值,T为时间,而K则是两种数值之间的换算关系。在不同的游戏里,K是不同的。K较高的游戏,意味着玩家付出同样的时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或者说,同样的游戏内容,K较高的游戏,需要付出的游戏时间就越短,说通俗点,肝度低,反之亦然。即使推广到不是RPG类型的游戏,这条价值公式同样具有效用:玩家付出了多少久的游戏时间,就应该给予多少的回报。K就是一个描述游戏系统中,由系统定义的、玩家通过游戏行为劳动所生产的单位时间的价值量。我称之为时间价值系数。
听到这里其实你大概有点知道了,游戏里的K值是由游戏开发者人为定义的。在实际开发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些辅助公式的修正,比如同样的时间,1分钟的跑路任务和1分钟的boss战,其劳动量是同质但不等价的,通常还会有各种辅助的公式进行修正。怎么进行修正呢?那你得问问育碧、卡普空、腾讯、网易这些公司的数值大佬们了,他们才是真的懂的人。前段时间卡普空申请了动态难度的专利,我相信这个动态难度的背后,也蕴含着相似的数值原理。一个数值系统完善游戏,可以把玩家各种行为规划好,并计算好相应的难度、路程,再通过大量的实验和测试,确定游戏的最终形态。牛逼的数值系统,可以相当精确地描述游戏的整体状态。我曾经在游戏公司工作时,我师父说,你只要告诉我服务器的玩家总战力之和,我可以给你算出来这个服务器每个月的营业收入大概是多少(仰望)。
但我要设问:数值的完善就是游戏的完善吗?
· 游戏体验的异化现象
Tynan Sylvester在《Designing Games: A Guide to Engineering Experiences》(《体验引擎:游戏设计全景探秘》)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击败兽人所得到的金币是一种外在奖励,因为金币本身和击败兽人这个行为无关。相比较而言,内在奖励和它所属的活动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击败兽人这种行为本身就会让人觉得愉悦,玩家就会因为这个内在奖励去击败兽人,即是并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奖励。这两种动机的效果应该是叠加的。如果你很享受击败兽人的过程,那么顺便获得一些金币感觉会更好,但实际上往往不是如此。研究表明,外在动机能够扭曲取代,甚至摧毁内在动机。让兽人掉落金币减少玩家自身想要击败兽人的渴望。
这个例子所讲的,正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体验是一种关乎人的感受,而数值则是一种用来表明物的关系的尺度。当体验被数值所取代,即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取代,就产生了异化。物的关系取代了人的关系,对体验的追求也被异化成了对物的追求。游戏在精妙的数值设计之下,实际上掩盖掉了很多本来游戏可以带给玩家的东西。把这个异化一般化到游戏的其他现象中也是如此。玩家对于角色的情感并非是机械的,实际上玩家会在玩游戏的时候投入相当真切的情感,有时候甚至要比现实生活的情感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感受,到了游戏中却往往只能以一个叫做好感度的数字来表达,而当游戏的演出被剥离后,你去看一看攻略,会发现好感度的背后也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和规则:送一个礼物就涨2点,答错一个问题就降3点,诸如此类。给它送同样的礼物,送20次,就把好感度刷满,但试问在现实中,谁会给好朋友连续送20次一样的礼物呢?
当你不上线游戏打副本,你可能就会被踢出公会,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公会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游戏内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则可能是为了保持公会的排名这种由游戏系统所定义的价值。又或者算是一些单机游戏,或许你真的并不是非常喜欢玩这款游戏,但你觉得你仅仅是想知道游戏故事的结局,于是不得不去把那些无聊、老套的关卡统统打通甚至全成就。我曾经接过一份兼职,为一些游戏媒体撰写游戏的评测文章。甲方会送你游戏(有时候可能是借账号),让你体验一下游戏,然后写一篇评测。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前我还在想完可能还面临违约的问题。在本来就带着不纯粹的目的去玩游戏,玩的时候也对游戏里本来该享受的内容变得挑挑拣拣,时不时要记得截图、记录,这非常破坏体验游戏时候的整体体验。物的关系(我和甲方的撰稿约定)取代了人的关系(我自己纯粹的游戏体验),也让我的游戏体验被强烈地异化了。
当然,我并非是反对数值设计,相反数值设计是游戏设计整个工程中相当精巧的一环,体现出了游戏设计中最理性的一面。但是滥用的数值设计最终导致的异化现象,也正是我们手里那些并不好玩、但又不得不上线爆肝的游戏的根源性问题或者说设计的固有矛盾之一。当游戏中存在任何资源交换的潜在行为可能性的时候,异化也必然伴随交换价值的产生而产生,异化是伴随交换价值的必然现象,当物取代了人,则形成游戏里的拜物教。
游戏系统与价值交换
Chris Crawford在《The Art of Computer Game Design 》一书中认为,一个游戏应具有以下特性:
冲突性(conflict)安全性(safety)交互性(interaction)表达性(representation)其中安全性本质上是一个界定游戏和非游戏的边界属性,是一个在游戏设计时不需要去讨论的,但是当你问何为游戏时又必须谈到的问题。
· 安全性边界
所谓安全性,我对它的解释是:游戏行为的结果对现实世界的映射的阻断。说人话就是:游戏参与者的游戏行为所带来的由系统规则产生的结果不会直接发生在现实中。一旦违背了这个原则,游戏的边界即被打破,游戏就不成立了。这里我们提到的安全,并不是仅仅只包含人身安全。我玩捉迷藏,我被鬼捉住了,我死了,但是“我死了”这个事件不会真的发生在现实世界,而是只发生在游戏世界内部。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正在玩老鹰捉小鸡,突然扮演老鹰的朋友捉一只小鸡的时候,把扮演小鸡的朋友抓伤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会立刻停止游戏。我打牌的时候,突然告知我打的不是分数而是人民币,我会立刻停下来离开牌局。游戏行为的结果产生了破坏安全性边界的效果,游戏行为就映射到现实了,那么游戏行为就不再成立。
但是这种安全性并非客观的,而是游戏参与者主观的认知。假如我俩是古罗马的奴隶主,我们分别让自己的奴隶去斗兽场角斗。对于我俩而言,我们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财产进行一场游戏而已;但对于奴隶而言,这可不是一场游戏,输掉是会丢掉性命的。但是对于已经放弃生命的人来说,生命也不过是游戏的筹码而已,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也是一场游戏。而当我们角斗正酣时突然告诉我们,有贵族为这场角斗下了巨大的赌资,赢的一方可以获得巨量的财富,输的则会被贬为奴隶,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毫无疑问打破了我们对于这场“游戏”的安全性认知,因为后果太严重了,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游戏的投入是安全的了。对于安全性的认知是一种游戏参与者的主观认知,衡量标准往往是参与者对于游戏投入的认知:这种投入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风险。
由于对于安全性
之所以在这里谈及安全性,是因为安全性界定了游戏系统的逻辑边界(指游戏规则所能够影响到的时空,区别于物理边界)。而界定了游戏系统的边界之后,就可以讨论一个价值作用域的问题:游戏系统本身产生的价值是伴随安全性而存在的。比如你游戏里赚的金币,是不能直接买你楼下小卖部的可乐的;而你手里的钱,也是无法直接买到动物森友会里面的家具的。现实与游戏之间存在一个明确的系统边界,这个边界区分开了两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游戏中的价值和现实中的价值,是无法通过游戏行为进行交换的。因为游戏行为是必须要具备安全性前提才成立的,一旦现实的价值进入游戏,或者游戏的价值进入现实,这个安全性前提就失效了,游戏行为的定义本身也就被打破,也不再能够被称之为游戏行为。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氪金。氪金是游戏中的行为,但它不是游戏行为,因为氪金在一般人看来,是打破了安全性前提的行为:我花了真金白银去购买游戏的内容。但是我们前文讲过安全性是具有主观性的,在氪金游戏中,理性的玩家是可以保持不过多花钱甚至0氪白嫖而毫无波澜。但是这种理性玩家几乎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绝对理性的人。就算是真的0氪玩家,也或多或少会在一些吃瘪的环节有氪金的念头或者冲动。但氪金游戏的设计师恰恰就是在某些地方设计了催生这种冲动的机制,让玩家上头,让他们的大脑在感性思维的冲击下无意识地模糊了安全性边界,在氪金的时候错把氪金这种理性上是非游戏行为的行为错认为是具有安全性的游戏行为。很多人说,氪金也是你情我愿的买卖,我并不这样认为。批判地说,处于冲动状态下的人是不存在你情我愿的,这时候的人完全被情绪支配,忘记了自己理性游戏的前提和初衷。
所以任何在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行为,都不是游戏行为。
红色部分是游戏行为,其余的连线都不是游戏行为。
· 现实世界的延伸:Meta世界
到了现在,实际上我们对于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划分已经不再准确了,因为二者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缓冲地带:互联网世界。游戏世界是一个深度虚拟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完全现实的世界,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由社交网络、大众传媒等非实体世界组成的信息世界(比如微博、贴吧、推特、脸书、P站、B站甚至淘宝、当当等等)。它们没有实体,但也因此换来了无穷无尽的信息空间。最近网上很火的一个词,元宇宙(Metauniverse),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很着迷美丽的物理世界,我觉得元宇宙不配Universe这个宏伟而美丽的词,《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间和空间的集合,怎么也不是元宇宙这个概念所能配得上的。我姑且在这篇文章里,将游戏与现实之间的信息世界地带叫做Meta世界。
Meta世界的存在,使得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价值交换更加复杂了。Meta世界的事物本身是没有独立的价值的,其价值必须要依托于现实世界的事物。电子图书馆并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收藏的书里的知识是可以用于现实世界的;我制作一个个人网站并不是为了制作而制作,而是为了在互联网上展示和留痕。Meta世界的事物,其价值根源必定是依托现实世界的,无论这个依托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游戏世界的价值也是如此,一切的游戏内容是为人服务的,大多数的游戏世界的价值是依托于人的审美价值而存在的(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价值,例如社交)。而游戏世界也同样可以向Meta世界交换价值,并且通过Meta世界作为价值的中介,找到现实世界的价值依托。比如游戏主播,通过自己的游戏行为(劳动)创造出直播画面(符号景观),通过Meta世界(直播平台)转播给观众,观众在现实中获得了审美体验(现实价值),主播也得到了直播收入(现实价值)。任何上层建筑系统,必须以经济系统为基础。
· 第三类价值交换
前文所讲,第一类价值交换,是玩家向游戏厂商购买游戏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无论是游戏软件、桌游卡牌还是球、毽、拍、绳等肢体、体育游戏的用具,本质上都是在购买生产符号景观的生产资料,是玩家用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价值和游戏厂商通过开发产生的价值的交换。第二类价值交换,是玩家通过游戏,付出时间、精力、情感,来生产符号景观来供自己使用,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的过程,是玩家劳动价值和凝聚在一幕幕符号景观当中的价值的交换。而第三类价值交换,则是玩家把自身生产的符号景观,通过一定的手段转变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把这些符号景观给同样有审美需求的其他人观看(比如直播、同人周边、攻略视频、游戏展会、IP授权等等)。
第一类价值交换:投币、买断、计时、内购、广告、订阅 、赛季 等付费机制第二类价值交换:玩法机制、演出机制 等游戏机制第三类价值交换:社交分享、游戏攻略、直播录播、游戏展会、周边模玩、游戏环境、同人作品、IP授权 等· 现实-游戏价值交换渠道:玩家的身份二重性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大规模的物-物价值交换关系,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游戏与现实之间直接进行虚拟和现实的物品交易的情况存在。现阶段的价值交换是以人-物价值交换的形式存在,即通过在游戏中积累资源,收益。而玩家在这个过程中,玩家作为一个人,他拥有现实和游戏的双重身份,藉此他才可以实现将游戏的价值转移到现实中去。而也是基于此,玩家可以把现实中的价值转移到游戏中去:比如呼朋唤友在游戏中开荒(当然,在游戏中和朋友一起开荒,朋友本身也是你的符号景观的背景板的内容物之一)。
当然,物-物价值交换之所以还没有在游戏当中大规模出现,是因为本身这种价值交换和游戏行为的定义是冲突的,即游戏中的价值必须透过人的游戏行为才能内化成审美价值,再由审美价值转化成现实里的价值。审美价值必然是人的审美,只有具体的人才能感受到具体的审美价值。
而物-物价值交换是直接跳过了人,在两个世界之间直接进行价值交换。假想一个你在《我的世界》里挖到的金矿,真的能拿到市场上去兜售而且价格不菲的情况,感觉如何?物-物价值交跳过了人,也就跳过了审美阶段,审美价值被抛弃。没有审美的冲动,游戏行为便失去了动机,本质上这种价值交换便不再具有游戏的属性了。
· Meta世界与游戏的本质区别
网上有非常多的对“元宇宙”的批评,但我认为大多数的批评是对其作为上层建筑的批评,或者是作为经济行为、资本行为的批评,但缺乏理论层面的批评。有人说Meta世界就是大一号的网络游戏,我并不完全认可。资本家们对“元宇宙”所做的期许与承诺,大家也看得多了。Meta世界不具备游戏世界的安全性边界,而且Meta世界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物质价值交换通道:物-物价值交换。一个数字的、虚拟的内容,可以像现实中的商品一样进行买卖。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我在XX西游、XX世界里卖金、卖装备、卖号干过的事儿吗?这不新鲜啊,都存在十几年了。然而事实是,这种交易行为只是小规模的、且基本上是去中心化的,本质上是没有人,没有法律会为这种交易来保证信用的。而我们这里提到的物-物价值交换通道,是一种大规模的、资本化的、甚至被法律保护的交易。就是说,你只要打开Meta世界的软件,就可以直接用游戏币点外卖。听起来挺好,那如果说老板用Meta世界的货币给你发工资呢?
其实到这里还是察觉不出Meta世界的威力,因为听起来不过是一套新的信用和货币、经济体系罢了。但Meta世界的真正的危险性,是在于我前文提到的K值——时间价值系数。
我说过,K值是由游戏系统自己根据设计需求定义的,也就是说,在游戏系统中,这个K值的多少是由游戏开发者(在现在的社会上,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概念替换为资本)直接定义的。也就是说,游戏里的东西值多少钱,是可以随意开价的。当然,它可能受到一定的市场规律约束,但是数字商品本身的可复制性以及市场规律本身也可能会为资本所左右,这种约束并非可靠的。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看看如今所谓的NFT商品,离谱的程度比我在文中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更可怕还是另一个问题,当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会带来异化。或者我们说得更简单一点:当一个游戏压根不好玩,但是里面的东西可以在现实世界兜售,请问作为玩家的你,作为玩家的我们,会做什么?游戏变成了一套套新的生产资料和挣钱工具,你还会去享受那种纯粹的快乐吗?
而身份,作为数字资产的一种类型,也会被重新定义。身份本身也会被数字化,通过数值来表达这个身份本身的人的属性。甚至可能实现数字永生——你的肉体死亡了,但是你的Meta形象和身份被保留了下来,而且“有人”不想让你死,于是你死了,但你又没有死。数字的身份作为物,掩盖了作为人的真实身份。远的不说,一些营销号的皮下换了多少人了,丝毫不影响这些营销号的人设、盈利模式。
所以Meta世界和游戏世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的。Meta世界可以建立一条直接的物-物价值交换通道,让人们去生产一些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符号景观,再把这些符号景观卖给那些需要这些景观的人。这种关系又把人本身的审美体验抛诸九霄云外,把本来脱实向虚的事物价值用K值定义到天价。用拟像代替过去描述物的符号,成为符号的符号,无限生产,无限收割。
游戏设计与三类异化
· 游戏设计的原理(简谈)
游戏在设计的过程中,由于创作主体性的存在,必然也就有设计目的的存在,即设计师希望给予玩家什么样的游戏体验。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存在一个根源性问题:玩家是如何产生体验的。
1. 体验与期待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情感是体验的未然,我觉得情感这个词有点歧义,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改成期待了。在游戏中,玩家的情感状态实际上只有体验和期待两种,体验是情感的进行时,期待是情感的未然时。
又或者,你可以将期待理解为情感的势能,而体验理解为情感的动能。这个比喻是极其合适的,因为如同物理中,势能与动能可以相互转化,体验与期待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我看到远处有座山,我会觉得,“哦,有座山”,但如果山上有座庙,我会像“咦?有座庙?”。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庙是一种人工的状态,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去探索庙里有什么东西。但当我期待庙宇的探索时,体验并没有产生,因为我还没有正式探索这个庙宇。而当我终于走到庙里开始探索之后,这种探索就把我之前对于探索的期待转化成了探索的体验。体验是玩家对于游戏的实际感受,而期待则构成了玩家游戏行为的动机,二者对立统一,互相矛盾,但又可以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玩家的情感。
2. 期待的产生
期待的产生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乎玩家价值观的问题。游戏设计的真正难点正在于此,玩家的价值观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的玩家价值观也必然不同,他们所呈现出的对游戏内容的期待情感也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玩家对于游戏内容的感知度、好奇心、沉浸感都是不一样的,而面向商业的游戏往往要在更多的玩家群体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就使得了解玩家的主体价值观这件事对于设计师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傲慢的设计师往往忽略了玩家作为人在游戏中的主体性。
玩家的主体价值观,源于三个层次:
(1)先天价值
饱腹、温暖、安全、繁殖,这是任何生物都在追求的基本生存要素。即使在游戏里,这些要素也是玩家对于游戏内容的基本追求。首先是你不能死,你才有资格继续游戏。于是我们对一些事物先天就有追求和排斥的欲望:果实鲜花往往意味着食物,所以色彩缤纷的东西往往更能吸引我们的眼球;尖牙利爪、荆棘刀剑往往是尖锐的,所以我们对三角形或者锐角的感知也更加敏锐;兽吼鸟鸣、流水雷电往往比环境的声音更加尖锐,我们对频率更高、音量更大的声音也有异常清晰的感知……这种能力是被刻进DNA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死亡搁浅》里面看见黄衣的米尔人会感觉到威胁;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荒野之息》里看见三角形、橙色光芒的神庙会很想过去;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死亡细胞》里暴击的钉钉声你不会觉得违和反而觉得很爽。
(2)后天价值
后天价值是源于玩家个人成长的经历所积累的价值观。初生的婴儿和原始部落的人都不知道钱的价值,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这些东西换来他们先天价值认为有用的东西的经历。财富、人脉、权力、情感、地位,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去换取更多的具有先天价值的事物。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人出生就知道的,而是要通过后天在社会中学习才能了解到的。这也是玩家的价值观千人千面的根源:每个玩家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后天价值观也是不同的,这让他们在选择游戏以及决定自己的游戏行为时表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多样性。
(3)系统价值
系统价值是游戏系统本身定义出来的价值,打死蛇会掉钱,这件事不是很奇怪吗?但是游戏的价值是游戏系统自己定义的,所以蛇死会掉钱就不奇怪,打蛇这件事就变得有价值了。现实中你在山里看到一条蛇,避之犹不及,何况去打死它?万一是个十年起步兽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第三百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请大家爱护野生动物)?
系统价值可以被定义,不过在实际设计中,为了不增加玩家的理解负担,很多设计师往往会选择一些约定俗成的价值范式来解决问题。比如游戏里的钱币往往也是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制成,以方便玩家理解它们的价值;重要的机关往往会闪烁以提醒玩家这里可以交互,出现休息区和存档点往往意味着前面有危险的陷阱或者boss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击败了怪物,掉落了鳞甲,然后卖掉鳞甲,得到了金币,我知道了鳞甲的价值,从此之后对于鳞甲,我都会产生想要的欲望。我在不断的失败中发现了一种攻击套路,这种套路最终让我胜利了,从此我开始期待遇到敌人,并且用这种套路击败敌人,甚至非常期待发现新的游戏套路。既有体验会更新我们对于游戏的价值认知,从而产生新的期待,这会产生一种循环:体验带来期待,期待产生行为,行为带来体验,……。
三类价值共同组成了玩家在游戏中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成为了让玩家产生期待情绪的燃料。不过,光有燃料是没有办法让车跑起来的,你还需要一个引擎:游戏机制。
游戏机制的设计的三个根源性问题
游戏机制的意义,或者说本质,即是给予玩家一个合理的期待-体验转化模式。玩家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于游戏设计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设计这样一套机制,因为它相当地抽象。但期待-体验的转化解释了几个问腿:
玩家为什么想要进行游戏行为游戏行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机制游戏行为既可以将期待转化为体验,也可以将体验转化为期待但是,游戏设计出了刚才说到的玩家价值观多样性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根源性问题:游戏体验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
所谓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理论。其内容是:物品的效用,对于具有一定欲望的某种消费者,会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不过,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学说,但我想魔改它一下,用在游戏设计中:对于同一个游戏内容,玩家对它的体验情感会随着体验次数增多而减弱。这种观点被学习理论所论证过,也符合实际的观察。我打一个怪物,一开始打败了它,很有成就感。但是随着系统给我分配任务,让我反反复复,每天刷50个,天天刷,我会觉得越来越无聊,成就感也荡然无存。我们可以列一个式子来理解,即:
期待 = 成果 – 期待中的成果
游戏行为的成果是客观的:打败了怪物就是打败了怪物,得到了金币就是得到了金币。但是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对自己的游戏行为进行一个成果上的预期,即我付出精力和时间去劳动,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成果。随着游戏的探索,做什么事会有什么成果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期待中的成果会越来越接近实际的成果。而期待也随之逐渐归零。简单来说,没有新花样,玩家迟早会对游戏产生厌倦。所以为什么很多游戏有随机这种机制:随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掩盖成果的固定性,以带来玩家对一个内容的持续期待。然而,当玩家把随机的规则也弄明白之后,最终的期待依然会归零:被完全摸清楚规律的随机也就不完全是随机了。
所以第二个根源性问题:任何游戏内容,只要玩家玩得足够久,都会被玩家穷尽。
而第三个根源性问题:情感是无法数字化的。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是一个数字化或者说倾向于数字化的系统。电子游戏以精准的逻辑和数学模型定义了整个系统的所有。然而,玩家是活人,人的情感是无法用数学描述的,正如同逻辑学可以用数学表达,但哲学不可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设计师不得不用数字来描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准确描述的问题,这个模型可以做到非常精妙,但却无法达到完美。正如同《黑客帝国》系列,架构师始终无法创造一个完美的母体来接纳所有的人类。
所以我们有了游戏设计中的三个根本性矛盾:
玩家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游戏内不可变机制的矛盾玩家对新内容的持续追求和游戏内容有限的矛盾玩家情感无法数字化和系统的精准性要求的矛盾我们看到的游戏设计的迭代变更,全都都能看到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影子。但很遗憾,这三个问题是游戏设计的根本矛盾,是无法完美解决的。如果解决了,那么游戏的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游戏设计令设计师们痛苦且痴迷的原因。
设计的异化
不过,这三种问题,在资本社会的作用下,也产生了异化。上文提到,游戏存在三类价值交换,这三类价值交换也对应了三次生产-产品-消费的过程。而只要有价值交换,就有商品存在。当商品存在的时候,就必然诞生商品拜物教,即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也就是异化。游戏存在三类价值交换,也就存在三类异化。
· 第一类异化:创作主体性的异化
现代游戏开发设计,无论有多么前卫的思想或者宏大的蓝图,依然要受到开发成本和销售利润的约束。资本在游戏的第一次价值转移的过程中,主导了游戏的生产、产品、消费方方面面。
生产侧
在生产侧,最破防的当然是无数的基层从业人员。游戏行业隶属于大互联网行业,员工加班到猝死的消息从来都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身居高位的业界领头人。对于资本而言为了达成其资本增殖的目的,必定会以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扩大资本周转规模、扩大剩余价值规模为目的来“改良”生产方式。
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无非两种: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完成的,简单来说,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是在规定工作时间外的生产,也就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加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比如2年开发完成的游戏,因为技术更新、管理优化等因素,在不延长规定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只用了1年半就完成了。而通过改进生产让生产效率高于社会平均生产效率,所得到的超额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超额剩余价值。
对于资本而言,往往是双轨并行,既要提高效率加快工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又要延长工时加班加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所以我们看到,劳资问题的新闻无非也就是两种:公司的管理变态(比如扣了alt键防止摸鱼,在厕所装计时器监控入厕时间等等),公司的加班变态(动辄996、007,长期睡眠不足)。我一个某大厂的朋友,有一天23点了,在群里说
“今天下班好早啊,要不要来一把?”
而内卷行为则是一种更令人叹为观止的行为:因为这是异化的异化。加班在形成企业文化的时候,本身就是生产数据对于生产过程的异化,用物的关系(工作时长)取代了人的关系(工作成果)。而内卷则是在企业文化本身也无法自洽的时候,资本无意识自发倡导的一种扭曲的价值。本质上,内卷是资本无法从劳动过程中榨取到超额剩余价值而导致自身的生产红利无法回馈到生产者手里时,所暴露出的自身的窘态。
但是对于游戏行业而言,对于生产侧的剥削是整个剥削的冰山一角而已,毕竟再在员工身上薅羊毛,也不如在用户那边薅羊毛来的快捷。实际上,尽管生产侧的剥削已经是非常残酷了,但在消费侧的剥削才是更令人瞠目结舌的。
消费侧
在消费侧,资本关心的是投入的资本和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地增殖资本的价值,为了不断增殖,资本家必须使他的资本不断地、周而复始的循环下去。这资本的循环,叫做资本的周转。周转得越快、周转时的资本积累越多,资本的增殖成果也就越大。而游戏产业的资本也遵循同样的而规律。游戏的消费形态转变、升级、迭代也都是遵循着这个逻辑在发展。
游戏的设计作为游戏生产的上层建筑,在宏观上是围绕着游戏厂商的资本周转发展而发展的。从过去的一体式家用机、投币制街机、买断制卡带机,再到点卡制网游、广告制游戏,再到现在的主流内购制游戏,以及新兴的订阅制和赛季制游戏。资本的周转周期一步步地加快,资本规模也越来越大,资本的增殖也随之膨胀。而在整个过程中,商业游戏设计无时不刻都在服从资本的规律。
街机打开了游戏市场的大门,但是相比起卡带机和买断制游戏,巨量的内容和在家就能玩的特点更吸引玩家,同时销售卡带比销售街机、赚取每次一个硬币的钱,更能让厂商赚到利润,买断制逐渐取代了投币制;而比起一锤子买卖的街机,持续收费、持续更新内容的点卡制网络游戏则具有更块的资本周转速度:本体开发同样长的事件,但每个新版本却只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可以做出来,并且可以持续丰富内容,吸引到更多玩家;内购制则打破了点卡制对于时间的线性依赖:点卡制玩多久给多少钱,而内购制则可以在短时间重复给无穷多的钱。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新奇的付费制度涌现出来,但一种消费形态是否会成为主流,依然要看期资本周转的速度和规模。在资本社会中,一种商业模式是否会成为主流,其选择的主导权依然在资本的手中。
我们消费者看似有用脚投票的权力:谁好玩,我买谁,爷高兴你管得着吗?但实际上,我们也是活在“母体”当中,资本市场给了我们一些看似真实的选择权,但是生产什么样的游戏,采取什么样的设计形态,把游戏做成什么样子,从来也不是玩家们说了算的。单机玩家骂了这么多年的内购制的劣行,也从未见内购制游戏消亡;一些厂商的恶劣行径罄竹难书,却也从未见其大厦倾覆。
产品异化
而在这种资本市场之下,异化就不可避免。街机游戏有很多难度变态的boss和关卡,这样子玩家才可以因为失去生命而投币;买断制游戏往往在宣传和游戏画面上下巨大的投资,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玩家来购买游戏,尽管可能游戏并不如宣传的那样酷炫;点卡制网络游戏中,系统往往只给你极其有限的瞬间传送手段,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玩家跑路的消费时间;内购制游戏则会出现大量的令人有消费欲望的设计:满屏的红圈数字,漂亮的角色和皮肤,战败后的强化按钮……不点名批评,欢迎评论补充。
厂商也无法克服游戏的三个根本矛盾:任何游戏都无法完全满足所有玩家、任何游戏的内容都是有限的,任何玩家的情感都是不可能用数字去精准描述的。而在资本的作用下,固有矛盾暴露出来,转变成了具体的矛盾:游戏设计逐渐数据导向,让市场上的游戏看起来大同小异,以求得不同玩家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为了持续更新而不把游戏本体做完,故意却一部分单独售卖,美其名曰DLC等等;用排行榜、战斗力等数字掩盖对玩家行为的评估,又或者用AI去捕捉并预测玩家的行为做一些针对性推送……这些异化有的客观上也促进了游戏设计的发展,但更多是暴露出厂商在现有的资本市场架构下,无法补足自身短板,或者说缺乏进取而存在的问题。
创作主体性的异化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表现,根本原因是游戏设计的大发展方向是服从于游戏资本的。微观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并不是服从于资本的游戏设计,这些设计有些可能会非常有影响力,但宏观上,设计依然是是被异化的,依然是资本导向的。
创作主体异化的特点
第一类异化发生于第一类价值交换的过程中。其本质依然是物的关系取代了人的关系,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游戏的商品逻辑主导了游戏的设计。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生产侧的设计师,还是产品侧的游戏,都受到了异化。除此之外,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受到资本的剩余价值剥削。两头挨打,赢麻了属于是。
· 第二类异化:生产主体性的异化
生产主体性的异化在符号景观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在3个层面:生产(玩)、消费(审美)、生产工具(游戏本体)。
游戏本体作为符号景观生产工具的异化
这一类异化源于第一类异化,即创作主体性的异化。在游戏作为产品销售给玩家时,其本身作为经过异化后的游戏开发过程的产物,必然也会将这种异化后的价值转移到符号景观的生产中去。比如通过游戏因为有限的内容,导致了开发者在游戏中制作巨量的无意义的、重复的行为:刷钱、刷材料、每日任务等等。作为符号景观生产工具本身,游戏自己在产品层面受到了异化,随后又将这种异化的价值观传递到了玩家身上:日复一日地在游戏里做着同样的任务,获得着同样的奖励,经历着早已厌倦的无聊体验。本质上,这种行为取代了游戏行为的原始动机:寻找乐趣,而成为了新时代游戏的动机:肝!肝就行了。这个道理带入到三种游戏设计的根源性矛盾都同样适用。
符号景观生产过程的异化
符号景观生产过程的异化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玩家投入生产的原料进行异化,一个是对玩家生产的目的进行异化。
人类的活动本质是对时间的支配。时间和精力是玩家投入游戏的必要材料。但现代游戏中,很多游戏鼓励玩家进行重复而无意义劳动,其实是把玩家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游戏生产的一部分,把玩家的空闲时间无意义填满。以此给予玩家一种正在生产,而且好玩的错觉。此外,又基于前文所讲的时间-价值等效原理,这种时间是可以被换成任何价值的,这些价值里就包含了现实的价值。于是,花钱买时间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也是点卡制、内购制游戏的付费设计的理论依据。
符号景观消费过程的异化
随后被资本的奶头乐所取代。打败怪物的成就感需要用数字来表达,玩家的技巧强弱被战斗力取代,追求自我实现的乐趣变成了一个个奖杯,而这些讲到的种种却只是虚无的数据和图片。随后,一些设计上的奇淫巧技被发明了出来:激起玩家的追求欲、挑拨玩家矛盾、故意制造麻烦让玩家不爽。负面情绪的设计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比乐趣本身更让人上头。玩家追求的乐趣被更加具体、物化的东西取代了,审美从对情感的追求变成了对物的追求。
· 第三类异化:身份二重性的异化
拜符号教
比起剥削打工的员工,剥削“打工的玩家”是资本更加喜欢的事情。玩家使用通过被剥削而换来的工资购买游戏内容,本身就是资本对人的二次剥削。而资本在这个环节为了让玩家心甘情愿地掏钱,则祭起了消费主义的大旗。给各种游戏贴上眼花缭乱的标签,通过媒体占据各种广告渠道增加曝光,这些都是太过于常规而不入眼的手段。现代游戏圈甚至形成了“拜符号教”。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廷作为神的人间代理者,解释着神的伟大,并且让艺术家们或雇佣或自发地创作神像、神画,把和神迹有关的物品称为圣物,供奉在华丽的教堂大殿之上。现在的游戏圈又何尝不是如此?声优+立绘创作出来的符号角色,把一个个“老婆”“老公”捏成塑料的神像,玩家们在自己的桌子上、书柜上摆成一圈又一圈,一排又一排;然后剥削那些比员工更好剥削的群体——同人,让他们自发地画着一张张神像、肝着一份份视频,发到社交网络后,在转发和评论里里齐声叫好;官方活动各种制作人签名T恤、海报,各式各样的周边玩具,拿回家后就拍张照放在那里;而玩家们通过各种“宗教秘术”——玄学抽卡,完成救赎券的购买,支付宝微信叮当一声响,灵魂便升入了天堂。
当然,玩家这么做纯粹是处于自身对于游戏、角色的喜爱(说实话,我也买,我边写边说,别骂了别骂了)。本质上,对于非游戏世界的游戏相关的消费,都是基于玩家自身对游戏中的内容的真挚情感发生的。但这种情感的表达需要物质上的载体和渠道,于是通过撰文、画像、手作等符号化的行为来完成自己的表达。这种价值实际上是在Meta世界里才存在的,而资本通过一定的手段,把这部分的价值许以众生,转移到了现实中。这么做当然不是慷慨,最终这些价值都要以消费的形式回到资本的口袋中。
教廷的牧师:身份捆绑的人们
资本会在现实世界寻求符号教的代言人。他们要足够驯化,能够把资本的价值观念分发给所有人,并且把资本希望让人们看到的符号景观散播到大地上。当然,人并不会那么顺从,于是资本就用金钱、合同,用好吃好喝将他们供养起来。等他们发现自己被这些东西牢牢捆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脱身了。各种画师、主播、up主、微博大V,各种KOL看似在互联网风生水起,但是他们一旦脱离了资本定义的语境,其自身的价值就会迅速退化。而有的KOL则是完全委身于资本,以至于脱离了资本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这两年主播和平台撕破脸最后被要求赔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劳务官司屡见不鲜,也说明了这些KOL们自身在生产的过程中被资本束缚捆绑。
原理上,资本把这些人们的价值都转移到资本自己定义的价值系统中去,通过价值迁移来让这些人们无法离开自身的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已经无关KOL们自己是否是心甘情愿了。最终资本想让你消失,你就可以小时,想让你再活过来,你也可以活过来。
符号景观的时代
游戏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缩影。物质的极大丰富让人应接不暇,感官的刺激盖过了对真理的思考,符号景观穿插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电脑的游戏里,在太古里的街景里,在旅行的照片里,在你桌上的手办里。物质太丰盛了,于是我们无法用单纯的物来理解他们,转而开始用符号去表达。而当符号也不尽其意,符号的符号——拟像则描绘了一个逼真的观念上的社会。拜物教早已全面升级为拜符号教,洪涛汹涌的信息自屏幕里奔涌而来,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用各种被资本定义的符号来描绘我们生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