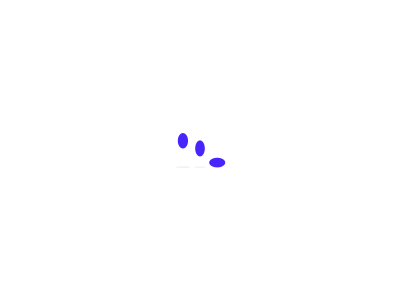三个下层的社会阶层跃居成长史,和她们疏离的信念当今世界
译者/玄奘法师
(一)
一炮而红后的刘军医师,病人嘴中的王秘书长、著名研究者,桑翁的看似“出急诊”。
假如你足够多幸运地,抢下了王医师的挂号,所以将有良机在周二的下午,赢得同他聊天的良机。
两个下午,100个病人,平均值每一病人能在王医师这儿赢得的诊治天数,不能少于3两分钟。
刘军提问病人的难题,快而急促,短小精悍。但假如你也是慕名而来来找他动手术的,那有很大的机率,会被婉拒。
“王大夫我慕名而来,大老远了。”
“我病人太多约不上。”
“你给我做我安心。”
“找我至少要等2到4个月。我就是建议手术,在哪儿做,找谁做,这个自己决定。”
“我就想找你!”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做不完。”
这就是王医师不爱出急诊的原因,他盛名在外,全国各地的病人赶到沈阳,希望能排到两个手术良机——但仅仅是医院内部“走后门”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塞给他的病人,刘军已经做不过来了。
两个下午的急诊下来,“收上来的病人,还没有得罪的人多”,因为“关系户”太多,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婉拒。
“每年主刀完成各类甲状腺及甲状旁腺手术近2000例,为目前辽宁省内每年完成甲状腺手术例数最多的外科医师。”
最多的时候,刘军一天手术量高达14台,从早晨7点多一直要站到晚上8点才能休息,“两腿发沉,感觉像支着两根木头棒子。”
刘军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秘书长。与这个头衔相比,王医师更看重一家名叫“好大夫”网站上面的评价。
刘军在医院内部也会赢得一些奖项,但他觉得没意思。“一群人戴着花,等着领导接见,领导来了,跟你照个相,然后拍屁股走了,你说有啥意思?”
“好大夫不一样,这是老百姓给的,病人两个两个给你评出来的,是你四五点钟起来,两个提问两个提问做出来的。”
在“好大夫”上,全中国的甲状腺外科,刘军排名第二位。排他前面的是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秘书长费健,只比他多了0.1的推荐度。
刘军很在乎这份荣誉,视为对自己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最高的赞美。
(二)
以上的故事,出自我刚刚读完的一本非虚构作品:《张医师与王医师》,这本书的译者是两位著名的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
这本书以庞大的细节,描写了90年代身处国企改革、城市去工业化等大变革下,三个下岗家庭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辗转腾挪。她们的父母使尽浑身解数,在时代崩塌、解体、堕落的过程中,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掉队,而且进入到富裕且专业的群体中,完成了难能可贵的社会阶层跃居。
张晓刚是本书的另一位主角,他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然后在301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秘书长。
刘军和张晓刚都是本书译者伊险峰的初中同学,当然,书中这三个名字采用的是化名。
三个人都是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出身,面对有限的资源,三个人都不负众望,成为社会专业人士,无论是其学历、职位、专业能力、社会地位还是财富收入水平,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精英社会阶层。
一炮而红后的刘军虽然不止一次在书中抱怨,忙碌的工作导致自己的生活毫无质量。
但高强度工作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王医师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水平。
在谈到自己女儿的将来时,刘军曾有以下表述:
“给女儿的留学钱?那才需要多少。假如(女儿)喜欢北京上海,买一套房,一千万够不?”
假如你熟悉东北人的说话方式,就明白王医师“一千万够不?”并不是一句疑问句,而是对自己所拥财富的一种轻描淡写式的展示(有些场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含蓄的炫耀),它其实是一句陈述句:
几百万的留学钱不算什么。在北上这样的一线城市里,我也有能力给女儿全款买一套品质不错的房子。
(刘军女儿一度希望离开沈阳,留在上海)
书中虽然没透露两位医师具体的年收入,但对著名三甲医院收入体系有所了解的朋友,不难猜到,这两位“著名研究者”级的外科副秘书长,年收入可以达到怎样的数量级。
更何况,刘军还有着近乎魔鬼般的勤奋,他两个人一年要操刀2000台手术,“相当于复旦肿瘤头颈外科全科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
年薪过百万,几乎是没什么争议的数字。至于到底是几百万,就像王医师谈到自己去外地做的手术量一样,“不能说得太具体,会有人觊觎。”
当然,这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社会阶层跃居励志书,译者用大量篇幅,呈现了两位医师完成社会阶层跃居之后的苦恼——信念当今世界的分裂、疏离,和一种不情不愿下“信念腐败”的过程。
“既不能忠实于自己的真实心意,与‘社会’保持距离,又掌握不了适度地沆瀣一气的复杂技巧。”
用李海鹏在本书序言的一句话总结,就是:
“我们都这么庸俗了,怎么还是不快乐”。
(三)
学历、能力、财富、名气、社会地位统统具备之后,张医师和王医师,仍像刚刚步入社会时一样:
最大的苦恼,是自己的姿态“不够社会”。
她们从小被要求奋进、诚实、正直自尊,但真正走入社会之后,不得不狼狈慌张地补习圆滑、世故、狡黠和复杂的说谎艺术。
“关系”、“社会”这三个东北最具深意的词汇,反而成了她们的噩梦
这可能是很多专业人士、社会精英和奖学金男孩,相同的苦恼与信念困境。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曾经的“乖孩子”,同样从小就被教育“人要凭真本事吃饭,投机钻营可鄙,溜须拍马可耻”——我对书中描写的两位医师面对社会时的苦恼、疏离和拧巴,感同身受。
我还记得,上大学时经常和几个好哥们讽刺吐槽几个学生会干部,我们给她们取了两个讽刺性外号:京巴(哈巴狗),几个学生会干部根据职级我们叫她们大巴、中巴、小巴……
因为我们觉得她们年纪轻轻,就满嘴官腔,一副部长做派十分恶心。
(谁年轻时希望成为王秘书呢?)
后来毕业了进电视台做记者,那还是在“十八大”之前,和官员们一起吃饭、喝酒是跑政府口记者的常态。
经常在酒桌上,我会感到无地自容。有时候这些人的马屁拍得我这个局外人,都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但这些人包括被拍的领导,似乎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这也是张医师和王医师所面临的信念困境,书中两位医师反复提及:
“要是会来事儿的话,(很多)难题就解决了。”
两位医师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也因为“不能来事儿”,付出了很多代价,遭受过不少社会毒打。
比如刘军毕业留院的时候,老师跟他说“你表现挺好”,结果刘军就傻呵呵地觉得难题不大,也不懂送礼。真毕业的时候,没留他,傻了。赶紧通过关系找到两个副院长,打了招呼,终于留院了。
张晓刚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毕业时成绩很好,但只能分到大连分院,结果连这个名额也被人顶了,又分到丹东的分院——张家最终通过关系,让张晓刚留到了总院。
比如刘军因为过于耿直,不够圆滑,在医院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领导。代价是,刘军很快遭遇到明火执仗的“小鞋”穿。他申报的科研基金,领导竟然说:
“我把你的项目报告整丢了。”
那是王医师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他一度考虑是不是要移民,在国外重头开始。
这就是二人信念危机的本质:
一种巨大的,个人无法忤逆的幻灭感。
因为在价值观层面,她们曾经所信奉的,和这个社会真正运行的逻辑,有着迥然的肌里。
她们恍然惊觉,父母学堂所教授的处事准则,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呈现近乎童话般的天真——
假如你执拗地试图要保持这种天真,则会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所疏远,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于是,从小到大,内心深处一直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出现摇摆,在这种令人痛苦的摇摆中,她们不得不以一种不情不愿的拧巴姿态,委身讨好并加入“她们”的当今世界。
(四)
成熟的说谎技巧、高超的接人待物能力,春风化雨般的巴结、谄媚和拍马屁的造诣,可攻可守的狡黠性……
所有这一切,在工人阶级子弟所受的教育中,都是缺失,甚至是被警惕、鄙夷和不耻的。
“奖学金男孩”努力奋斗的两个下层动力,就是希望跳出父辈社会中,凡事都要找关系、拼背景的潜规则体系,她们希望能够凭真本事吃饭,靠学识和专业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但当她们走上社会才发现,虽然博士学位给了她们比父辈更高的起点,但本质上,她们并未能跳出那个令人厌恶,却无所不在的“关系网”。
她们蓦然惊觉,这个社会,并不是说你有好的学历,有业务过硬的专业水准,就可以如鱼得水。相反,真正在社会上可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反而是教育观念中那种一直被立为“小人”的形象。
有时候,“她们”仅凭潜规则拉关系,“耍嘴皮子”就能赢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和资源。甚至,凭溜须拍马轻而易举地将原本属于你的东西,毫不脸红地抢过来。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其价值观出场设置为善良、耿直、心口如一等“君子”参数的张医师和王医师,当然会感到某种幻灭。
举两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
就是你从小到大的教育,无时无刻都在告诫你,做人应该像海瑞一样。当你真的走上社会之后,在碰得头破血流之际,失望地发现, 像和珅一样八面玲珑才是两个“社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正如王医师无比厌倦“混社会”,他仍试图保持一种专业人士的“清高”:
“哪个科长来了,处长来了,我愿意搭理你就搭理你,不愿意搭理就不搭理。我不用巴结你,不用说小话。我没啥求你的。”
但谈到女儿时,王医师的清高会瞬间被击碎,他说“女儿是我的软肋”,假如女儿将来也学医:
“我就得违心,就得跟她们喝酒,拉关系。我现在奋斗一年顶我女儿奋斗多少年?”
于是,两位医师不得不完成自己的中年蜕变,她们终于变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人物:
“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
这儿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